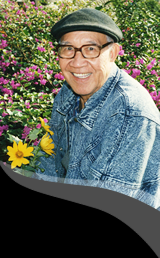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大智若愚
伍法岳第一次見到孫觀漢先生是在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我正在清華大學核子科學研究所就讀。那時清華大學在臺復校只有兩年,無論師資、校舍,或是儀器設備,都不能與今日的清華相比。孫先生的到來,是校中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我們二年級研究生,正要開始碩士論文的寫作,尚不知如何著手,大家都覺得這位海外學者回來,至少是論文有著落了。
記得在孫先生抵達新竹後不久,我與郭子斯是第一個去見他,要求他指導論文,在略作交談後,孫先生就欣然應允。想來當時孫先生對於國內師資欠缺的情形,還不甚清楚,研究生要跟他工作,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可是之後不久,大約是班上的十幾個同都向他作了同一要求以後,孫先生逐漸瞭解了我們的情形,一天,忽然在課堂上對我們說,在美國的教授,一般也不過指導幾個研究生,現在十幾個都要跟他作論文,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在清華與孫先生的接觸,先後不到一年,但是孫先生帶給我們的新知識,新方法,與新觀念,是不能以時間來計算的。除了課堂上的講授,(當時孫先生擔任我們二年級的「保健物理」一課),孫先生教了我們最重要的,是作人作事的方法及道理。他的實事求是,講求效率的精神,當時作學生的我們見了,為之耳目一新,而論文指導的事,就是第一個例子。
對於我們幾乎是全班一致請他指導論文的要求,孫先生毫不加以規避,立刻認真地去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他將我們按興趣分為兩人或一人一組,分別給以研究課題,然後指導如何收集參考資料和實驗步驟,並著手向國外訂購材料及儀器。能省的就省,能共用的就共用,由於他對國外廠商的熟悉,不幾個月,各項器材就紛紛運到了清華園。記得次年(一九五九)四月校慶日時,我們每一組都有了像樣的陳列展現給校友,而每人的論文,也都順利如期完成。其中好幾篇,包括郭子斯與我的「慢中子測定法」一文,日後都在國外的期刊上刊登。
一九五八年與孫先生同時返國的,還有他的夫人勞娜女士與兩位公子,那時只有十三、四歲吧!勞娜對於我們同學的生活也很關切,除了給同學們補習英語,還教以國外的生活細節,以及出國前應有的準備,甚至還給每人一個順口的洋名。對於我們的申請學校,孫先生與勞娜則更提供意見,寫介紹信。就是憑孫先生的一封信,匹茲堡大學物理系就給了我一份獎學金,(我後來選擇了另一個學校,至今仍覺過意不去),回想起來,那段時間的相處真是親如一家人。
一九五九年我到美升學,由於研究及教學的忙碌,此後與孫先生只見面了幾次,但是由於在清華相處的那段感情,我們保持了信函及電話的連繫,除了談論到學術及國事上的問題之外,孫先生還經常教以作人作事的道理,使我受益良多,而對我啟示最大,感觸最深的,莫過於他對於素未謀面的柏楊先生所付出的精力與熱情。
孫先生與柏楊的一段交往,自最初的神交,以至在國外的努力奔走營救,到最近的晤面要一部傳奇小說才能說得清楚。這裡我只提出幾件我知道的小事,作為日後歷史家的印證。
柏楊入獄後,除了妻離子散之外,更受到朋友們的規避,只有他的學生陳麗真女士,在極不順遂的環境下,給予他適當的照顧。獄中的書信經過檢查,孫先生的信件自然無法交到柏楊手中,甚至連孫先生給陳女士的信,也給收件人帶來極大的困擾,常為當局傳問。這時的孫先生是苦悶極了,陳女士處不更去信,寄信當局的投書,則是有去無回,而柏楊更是生死未卜,甚至海外報章還刊出他已被處決的消息。這段時期內,我因有返臺之便,常自陳女士處帶來柏楊情形的口信,有一次還帶回了柏楊的手筆,證明了流言的不實,孫先生因此曾去函要求更正,足見孫先生的求真精神。
為了柏楊的事,孫先生在國外奔走不遺餘力,包括協助柏楊的著作在海外出版。柏楊入獄後,他的著作在國內是已絕跡了,這時有香港的文藝書屋某君,據云是柏楊的友人,有意在港發行柏楊的舊著,知道了孫先生對於柏楊的關切,去信向孫先生要求資助,孫先生立即寄去了六百美元。自此柏著在海外風行暢銷,不數年即需再版。此時文藝書屋以印刷費用過高為詞,又向孫先生要求補助。當我勸孫先生,姑不論初版的盈餘多少,至少書商沒有版稅的支付,這種沒本錢的發行,似乎沒有再資助的必要。未料孫先生在電話中笑笑說:「我們不與這些生意人爭論,只要他願意出版,出點錢也行。」於是又寄去六百美元作再版的費用,也許一般人認為這是書呆子的想法,可是仔細想想,這才是真正的「大智若愚」呢!
孫先生營救柏楊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是本著他的一腔愛國熱誠,當初很少有人料到柏楊真有被釋放的一日,至於柏楊在軟禁於綠島的情況下,終能回到臺北,重拾舊日的筆桿,我可以肯定的說,完全是孫先生的努力所致,其中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必定不少。只望有心的歷史家能早日執筆,讓我們早早讀到一部傳寄的全部內容。
一九八○年八月於波士頓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