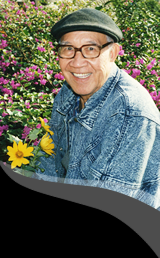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人文主義的清道夫
曾華璧
孫觀漢是一位具有良知和社會知名度的人物,但是他平易近人的氣質,卻常常令人忘了他曾經擁有輝煌的事業紀錄──例如在科學界他個人有四十多種專利發明權,在國內他更被尊稱為原子科學之父。多年前,我因緣際會在清華大學短短兩年的任教生涯中,有幸認識孫觀漢先生,爾後的交往,對我個人的思想觀念,
和許多孫觀漢先生的老朋友們相比,我和他相處的時間實在不算長,因為這期間我曾經飄洋過海,在美國麻州的康橋生活四年。回國後,任教於交通大學。交大與清華園雖只是咫尺之隔,但因忙於教學工作,又要往返新竹與台北,所以並沒有天天見面、互道安好的機會。不過每次互通電話或相聚,他依然是那麼親切,充滿智慧。
一九八二年我出國之前,曾經寫過一篇「孫觀漢先生──中國原子科學之父」,這篇文章採用類似傳記的寫法,比較偏重於綜合整理孫先生過往的心路歷程。今天有機會再度執筆,則希望藉著親身的經驗,對孫先生「志」與「道」,作個人觀點的抒發。事實上,孫先生令人稱述的優點,相信凡是認識他的人,都可以作見證;而我的本意只是希望忠實記錄自己的觀察與感受而已,並不是要塑造一尊讓人供奉的「菩薩」!
姑且撇開他輝煌的歷史與事功,這位長年足踏布鞋,身著便衫,近年來困於腳疾的老先生,到底具有什麼特質?竟然能夠讓許多人樂於接近他。基本上,我認為他是一位有智慧的長者,通達人情世故,不攀附權貴,淡泊名利,生活簡樸,謙虛為懷,熱愛社會,更有關懷民族文化發展的高貴情操。在目前富裕的台灣社會中,現實功利主義當道,像孫先生這種有思想、有文化,卻能安貧樂道的,真是難能可貴。這使我想起一種世界新趨勢:大約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有識之士鑑於工業革命發生以來,科技發展已對人類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的破壞,於是推動一種新的科技哲學─也就是崇尚謙卑、簡樸的生活理念,呼籲人類慈悲、節約,以盡量減少對地球資源的破破壞與消耗。孫觀漢先生一生兼受中西文化薰陶,因此具有西式科學家與中式哲學家的氣質。從他的人生哲學與現實生活的履踐上,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有陶淵明之志,而行事作為更與當代新科技哲學理念不謀而合。
孫觀漢先生有相當豐富的人文情懷,足以做為科技文化掛師者的反省與效法之典範。在他的文章中,我們看不到濫情泛愛,或是八股式的愚忠,而是針對問題提出懇切而發人深省的批判。我認為他是一位為社會掃污的人文主義清道夫,筆鋒攻打充斥於我們社會的愚、昏、髒、亂。多年來他苦口婆心所揭發的問題,諸如:公筷母匙、蒼蠅文化、談不勝痰的「痰文化」,以及無公德的文化等等,無一不是基於掃污的理念。在他的思想裡,他認為「老昏病」三個字可以充分說明中國社會文化弊病的癥結所在。但是年復一年,由五四時代的魯訊、到柏楊,到他回台長居清華園,這段將近十年的歲月,中國人的民族性、社會劣習等等問題,人人同心感受,同聲批評,但仍然難有立即改善之效,難怪他在傷懷之餘要痛苦地問:何時可以成立老昏病研究所?而這不也是關心中國民族發展者的相同慨歎嗎?
在思量人類的尊嚴問題上,孫觀漢先生特別呼籲大家「尊重人權」─也就是尊重人類的生存之權,並且要促使人類的生活智慧化。他認為有此二者,方能使我們達到「現代」的現代化,此一理念與情懷一直是他為文倡導的重點,而我自己感受的這種精神則特別深刻,去年(一九八八)暑假我正忙於準備開授一門新課─「科技與社會」,探討工業革命以來科技對人文、社會的衝擊。我將課程綱要拿去請教他。孫先生很客氣的直說懂得不多,但一方面則相當嚴肅的提醒我:不論世人有多大的聰明才智,若是不能注意原子彈對世界人類的生存與文明的威脅,則一切枉然。我同意此一見解,所以對於他的告誡特別警惕,且牢記在心,並在日後的課程中,在討論「科技發展對人類之威脅與控制」乙節裡,將此信念提出。
沒多久「河殤」一文在當年暑假推出,在台灣引起強烈的震撼,討論「河殤」的文章,多如過江之鯽。孫先生才在今年元月四日中國時報「覓覓集」專欄中,發展一篇標題極為普通、平凡的「從河殤談起」,內容發人深省。基本上,孫先生同情「河殤」所談的問題是「中國人最深沈的長嘆」,不過他進一步揭舉二個深值注意的問題,簡言之,就是「人殤」與「核殤」。他認為中國民族聰明有餘,智慧不足,若是不能根除「老昏病」的各種劣根性,萬一將高等文化發展成殺人文化,「河殤」不就成了「人殤」?另一方面,西方工業文明並未將科技文化變成「人類」的文明,核彈的發明,已帶引整個人類到滅亡的邊緣。他不禁要說:「比『河殤』要嚴重萬千倍的『核殤』,大家似乎不覺得它的存在,這種缺乏智慧的愚蠢和深沈的病痾,才是我們的浩嘆!」誠哉斯言!
孫觀漢先生對近年來台灣社會價值的丕變,有很大的感觸。固然在科技進步下的後工業社會,講究短、小、輕、薄,台灣人喜愛飆車的快速感就是一個明證,但也正因為如此,這個社會也就變得膚淺、短視,精神生活十分貧乏。有一次我提出想讓同學們由黃仁宇的「萬曆十五」一書來深入探討中國的皇帝制度與傳統政治的種種問題,這位曾經一再批評「中國帝王專制史堂堂皇皇地遮蓋了人民的飢餓史」的孫觀漢先生,又頗具深意的提出他的見解,他建議我出道這樣的題目:「論一九八九年台灣股市飆漲對中國文化之影響」。由此可見他對台灣近期社會發展之關切。
事實上,人類的尊嚴與存亡之真義,文化的發展與興衰之本質,是孫觀漢先生長久不變的終極關懷,在我的心中,孫先生一方面見證著當代歷史的演進,一方面則不斷的提出諄諄警語,來監管維護社會之發展,他有時不免傷懷,但終不改其志,這種精神令我敬佩。
作為一位歷史的學習者,我非常喜愛孫觀漢先生的「黑白球」的觀念。歷史的演進有它的「常」與「變」,而歷史人物之得失與否泰,都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一時現象,並不能改變其存在的基本本質。「黑白球」所宣示的觀念是:事物的本質不變,觀察的角度不同會導致不同的結論,因此人要避免主觀、武斷。歷史的信念也強調客觀、同情的諒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等,這些理念,彼此之間有相謀合之處,也是處世待人的好準則。
國父孫中山先生和魯訊,原都立志習醫救人,但最終卻棄醫人之業,轉而致力於醫國的崇高理想。孫觀漢先生原本以科學工作的成果回報社稷,但在圓滿完成事業的第一階段之後,卻以觀察社會,提出諍言為新職志。這種情懷除了受到柏楊先生的影響之外,多少也是受到醫國精神的感召。所以,近十年來,他視中國人堅守阿Q陣地,不能放棄纏小腳文化的弊病為民族社會的沈痾,苦口婆心地提醒大家注意改正。羊牧先生對孫先生這種鍥而不捨的傻勁,忍不住比喻他是「中國的唐吉訶德」,而中國的「老昏病」就是他的風車。此外,劉俠女士稱呼孫先生是可愛的清道夫,實在是非常貼切的描述。
我時常想,孫先生並不是一朵嬌豔的紅花,但絕對是一棵蒼勁有力的老松。這棵有心、有愛、有智慧的長青樹,使他成為許多朋友心中敬重的長者,而他的精神、他的志業、他的情懷,更使他無愧於成為社會之瑰寶。也正因為他有心,所以他不滿意人類的成績單,不過有許多時候我不禁地想:孫觀漢先生個人的成績單,是否對我們的人生理念作了什麼提示呢?
一九八九.八.台北「文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