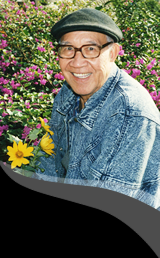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關懷與愛心
李玉珍
新竹清華大學百齡堂後方的教授乙舍,一樓有扇擺滿盆景,綠意盎然的窗臺,那裡就是孫觀漢先生溫馨的小世界,永遠對有心,有愛的人敞開著。春寒料峭的清晨,眾人好夢正酣,孫先生卻在四、五點就展開了一天的工作,許多觸目有感的作品就是完成於晨光中;六點準時出門散步,順便買一套熱烘烘的燒餅油條回去,偶爾還喜歡摘些自種的清香凝露桂花,添得一室酣香。孫先生酒品高雅,千杯不醉,深得梅貽琦校長真傳,往往以酒代茶,以酒會友,最喜金門高粱,認為是世界至品!
孫先生自一九六七年起,陸陸續續出版了些非科學性的感性雜文,如「關懷與愛心」(即「菜園懷臺雜思」)「菜園裡的心痕」「菜園拾愛」「有心的地方」,目前還常在中華日報發表文章。令人矚目的,孫先生是中國原子科學之父,清華在新竹復校時,他鋤草搬磚,也是首創人之一;一九五八年又協助清華建造臺灣的第一座原子爐。世界聞名的用閃爍計數計測定中子,藉隕石粒子測出月球自行發光的發韌者,也是孫先生。他同是費十年的功夫,發明許多新式玻璃,孜孜不倦地完成一百多篇科學論文和四十多種美國專利,而只從西屋公司獲取象徵性的一元美金。
第一次見面,孫先生卻出乎我想像的平易可親。他滿臉笑容地等候我們,一身褐色舊毛衣,步鞋,稍微瘦小的體格,尤其皚皚的白髮和紅潤的雙頰映照之下,令人聯想起家鄉的老祖父。再等孫先生亦詼亦諧的眼神流露出關切時,我忍俊不已地憶起老神童周伯通,禁不住「孫伯伯好」!脫口而出,從此我們在清華園中,又發現了一位亦師亦友的長者。
孫伯伯於一九一四年六月誕生在孫端,是浙江省紹興縣城附近的村落,一九三六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工系,立即考取清華留美獎學金,並和張明哲校長同榜赴美,榮獲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曾任美國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室主任。今年六十九歲,去國四十四年,對祖國的緬懷和熱愛,卻未曾因時而減,甚至自許:「中國是我的娘家,美國是我的夫家。……有時娘家缺點煤米油鹽,或認為小腳很美時,正是出嫁的女兒盡點義務,說點話的時候。」
將近半世紀的美國式生活,使他比美國人更美國化,他卻採取了中國人凡事包容、凡事體諒的態度來批評,這點著實可貴。以下就是訪問的內容。
「我想問你們,讀書的目的是什麼?」孫伯伯搶先機,反問我們。「紹興國語」又將了一軍,幸好三兩句就熟悉了。大家很有默契想轉局,結果孫伯伯點起名來,又頻頻地倒酒,要訪問的人反而霹霹啪啪搶答了。
孫伯伯總結說:「讀書是要抓住重點。我覺得中國人很會讀書,用不到我來多說;不過讀書除了求名利外,還有什麼?你們回去後,不妨想一想。今天我稍微可同你們談的,是做人的心得。因為我的情形和一般人不同,浙江大學畢業一年後,就去美國,一待四十四年,所以可比較客觀地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早已司空見慣的壞習慣。
「中國人照我的觀察都很聰明,但是為什麼三百年來,還弄不好?經濟趕不上日本,民主制度不如美國?」
中國在臺灣三十年來的經濟奇蹟,不正是例證嗎?
「讓我們試著把眼界放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殘破不堪,如何從無到有?而根據一位旅居日本三十年的中央社記者李嘉先生的觀察,中國人還是比日本人聰明!所以我提這個問題該是公道吧?」
孫伯伯反應靈敏,又注重發掘問題,討論時大家常不自覺地群起自衛,很符合族性,卻不知這種反射動作,是否受限於傳統灌輸我們的思考方式?
「中國人不能合作,自我觀念特重,如臺灣的小型貿易公司就有幾千家之多,拚命競爭,結果自相殘殺。」
這歸咎於自私。一切在自私自我中生活的人,成就自然有限。
「別人也自私呀!但是我們這種淺薄或過分的自私,從何而來?若老花精力想佔人便宜,聰明反被聰明誤,就精明得笨了。譬如一堆垃圾不處理掉,倒在別人門前又被推回來,還不是於事無補。」提及公德問題,突然想起「你丟我撿」,諸如此類「博愛」的口號,響徹在蒼蠅橫飛的街道上,竟是痛心的沈默了。
「神君觀念也是很可怕的,君主一人專制,就決定所有人的命運。更奇怪的是,這麼可恥的錯誤,居然視若無睹的延展五千年。」
在另方面看,日本人的天皇制度和武士道精神,似乎有利於吸收工業革命的影響。
「可能日本人知道合作,中國人像一盤散沙,喜歡各自為政。日本民族也沒大什麼大智力,道德教訓學中國,科技學西方;他們的經濟繁榮,優於我們卻是事實。什麼原因造成的?」
翻閱中國近代滄桑的一頁,過多的人口瀕於饑餓邊緣,造成了落後吧!
「貧窮沒關係,重要的是心態。譬如三年前我參觀萬里長城,共產黨一向階級嚴格劃分,但外賓有專用廁所,並且仍骯髒的很。我看到那裡水多,人工便宜,可是就掃不乾淨。所以觀念的改變要比物質享受重要多了。」
「中國人缺乏適度的自尊自重。唐人街的廣東人稱美國人為『番鬼』,不是太自大欺人了嗎?即使自己真的了不起,也應該幫助未達理想的人。」
孫伯伯很邏輯化地分析,他尊敬事實,看不慣口是心非,強調的只有一個字─做!讓我回想起虛擲光陰的態度,不免心焦如焚。事實勝於雄辯,別人很容易以你的成果衡量你,而平日司空見慣的動作,此時此劇湧向心頭,竟不再瀟灑,而成為「孰可忍與孰不可忍」的嚴肅掙扎了。大家從小就會阿Q的說:「眼不見為淨。」「不乾不淨,吃了沒病。」但是孫伯伯卻熱誠地,用放射線驗出,中國人的吃飯方式,大家互相交換口水,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該告訴你們的,免得以後吃不到漂亮女孩的口水了。」
那麼,中國為什麼康樂不起來?怎麼能康樂起來!
「中國人很聰明,卻弄不好?因為聰明和智慧是不同的,智慧的定義我定為:把聰明才智用在美好的方面。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學上多的是例子。像秦檜和袁世凱不都能翻雲覆雨嗎?可惜不知善用天資,做壞人的魚肉百姓,弄得萬世罵名。所以我們不謹慎運用聰明,是很可怕的。」
氣氛突然凝結,默然以對。人難免都護短,心中充滿了衝突時,遽然扯下面具,迎對種種缺失,才肯痛改前非。孫伯伯試圖講笑話來打破沈默,卻又接觸到更尖銳的問題。
「我的美國同事問某某中國教授:『你有幾個孩子?』他居然回答:『我沒有孩子,只有兩個女兒。』這不是笑話嗎?堂堂高級知識份子,仍不拿女人當人看。」
孫伯伯最近即將出版一本「我看中國女人」,便出自細膩的體驗中國女人難為,進而欣佩其溫柔敦厚的美了。
「我的結論是─(故作停頓,頑皮的眼神又流露了。)第一,中國女人很好看;第二,中國的將來靠女人。」
現場的男士起鬨了,傳統的包袱太重了。有人問:「應該是男女合作,女男平等吧?」
「女人已經和男人合作五千年,結果如此,也該讓女人出頭了。首先無可否認,母親是女人。母親又最具實際影響力,任勞任怨,體貼入微的愛心。雖然女性未必盡善盡美,譬如我所知的,某位新女性,曾活躍於淪陷前的上海,領導女性參政工作,卻偏偏看不起女性。
「不過,再壞的女人像武則天、慈禧太后,也並不會比其他昏庸的男皇帝糟到那兒,我們不能說女人比男人更壞。
「男性可以從傳統的觀念來反對,因為他們一向當家。直到目前,看輕女人的這種心態,在社會上還是很普遍。」
孫伯伯更進一步說:「有心的地方就會有愛,有愛的地方就會有美。」的確,愛是人與人之間真正可能聯繫的途徑,失去愛心,人類只有掉落於錯誤、褊狹和自私自利的痛苦深淵,萬劫不復了。
孫伯母勞娜女士,是實驗室裡的同事,專攻數學,目前仍在任教於美國某中學。她非常尊重子女(長子世亞、次子世樂和小女兒世鍾,後二年者均獻身醫學研究)。縱使是一封令人焦急枯候的入學通知,世樂沒回家,捏著信也絕不私自開啟。
「我們的勤勞儉樸和對小孩的愛敬並重,不但平素少洋味,並且含有極濃的中國鄉間純厚優美的風氣。但在做事方面,我們的態度,卻幾乎完全相反,我們力求負責,力求效率的提高。」怪不得梅貽琦校長稱讚他是完全美國作風。
「教育孩子真難呀!有位中國朋友得意洋洋的說:不打不成器。但是我卻寧願用愛來管束小孩,從小到大,不打一下。這在美國的家庭環境中,最做得到的。從小開始,家庭就得具教育的理想,不要讓他習慣見怪不怪。」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孫伯伯一九六七年就始開呼籲,「廢除國小惡補,」在他認為,「教育即是救國的治本工作。」
「中國人的自我觀念、忽視公德,和教育密切相關。尊重傳統,崇拜權威的思想教育,根探蒂固,以為讀書最高尚,而一味追求名利,爭權奪利,忽略人際協調的重要性。不能自尊自信,便也不信任對方。父母不承認子女獨立的人格,子女也凡事依賴,不願獨自面對事實,甚至拒絕接納他人的想法。
「我常開玩笑,要把你們從熟悉的環境趕出去,到美國去走走。學習科技很熱門,不必我講,但是更重要的,去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人,正在做些什麼?他們怎樣做人?」
清華畢業生出國率很高,孫伯伯總是盡力幫忙,或者慷慨解囊。但是回國率多少?
「這是我們教育失敗的地方。讀書很辛苦,同學往往認為大學教育是自己考試競爭得到的,沒考慮國家每年支出龐大的教育費用,眼光便侷促在個人的名利。」
「至於留學生回國的問題,幾年前我問過清華學生:『你們抱怨師資不好,那麼五年後你獲得學位,肯不肯回校任教呢?』設身處地,你自己呢?」
「報國的途徑很多,不需要搖旗吶喊,是要自己肯定正視問題,親自去想、去做。所以留學生應回國否?當依他們對自己、對國家的認識和愛護,作唯一的先決條件。」
中國的一位大文學家徐訏先生,形容孫伯伯「像個老太太般的苦口婆心」,習慣用英文書寫科學論文的人,中文雜感卻寫得明白曉暢,功力不可菲薄。更令人欽佩的,把冷冰冰的科學精神,關注照應整體社會,誠懇踏實一如菜圃老農。科學和人文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嗎?孫伯伯開放的心態,可供給清華人學習。
讓我引用「傅鐘二十二響」來形容孫伯伯的生活態度。傅斯年先生認為,每人每天至少應花二小時來思考。孫伯伯正是如此用心地生活。親切的一席話中,他有一種將國家社會大事「閒話家常」的本領。悠閒而一針見血談吐,不浪費一分一秒。誘導你一起思考。依稀彷彿,自己也曾閱讀過報紙刊載的資料,孫伯伯先想到先用了。一番腦力激盪後,遺留下滿腦待解的問號。
孫伯伯具有美國式明朗的急躁:「你的理由很多很好,但是做的成果在那裡?」並且包含中國人的恕道,謙虛誠懇,始終如一。所以他能擁有許多忘年之交,不分男女老幼、膚色背景,皆有如沐春風之感。這樣的魅力,何止言語溝通而已,更歸功於他平等、公正的人格。譬如外國學生和老師在課堂上辯論,態度不卑不亢,言之成理,孫伯伯並不認為這就違反尊師重道的原則了,反之他認為這是師生間應有的態度!
他老人家曾傷心地說:「了解我觀點的國人,很少很少!」其實大家都太了解這些事了,關鍵在於有誰能夠、願意去真實而徹底的做呢?人之尊貴在於能思想,能改造環境,所以有正面表達意見之必要,有發揮要個人才情,追求真善美的權利。若太安於「天命」,僅止於解釋和容忍既成的現象,無異故步自封,苟安一時。無論任何藝術、科技的創造,不免遭遇瓶頸階段,而一旦突破,便是峰迴路轉,青山綠水,更上一重天。身為知識份子,身體力行是當務之急。
漫漫談來,方覺剖析別人的思想,何等困難。只希望在晦暗不明的成長過程中,學習到孫伯伯的一絲一毫。不只期許內在的圓融,更迫不及待的,實際訓練個人的生活態度。或許你正苦於大小考的追殺不停,正埋頭於計算機中心,挑燈夜戰,都懇切地邀請你,甚至在你庸庸碌碌的追求名利,當清夜夢迴時,可把你的感觸更深一層地思考。因為唯有我們願意發問時,才能體會孫伯伯那種觀看的焦慮,進而親自要求整體存在的價值。容我再叮嚀一聲:儘快去實現你的理想!儘快去認識孫伯伯吧!你將會得到意外豐盈的收穫。
一九八三年四月新竹「清華人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