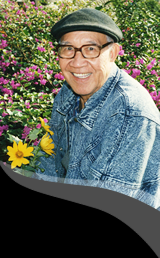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愛心的實踐
陳忠義
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一艘外商的小輪船把一百多個留學生自上海外灘載到吳淞口外,那時「七七蘆溝橋事變」剛爆發不久,日本軍閥正瘋狂大舉侵華的前夕,上海情勢非常緊急,黃浦江上日本軍艦,包括出雲旗艦,它們的砲口正對著閘北方向的國軍。
當這艘外商輪船與日艦擦身而過,船上有一位留學生心中充滿著慚愧與悲憤,慚愧的是「目擊敵人的槍砲在國土內對著同胞和軍士,而我們卻在外商的庇護下,竟揚長而去。」悲憤的是「與日艦相隔只幾十丈,恨不得一拳打去,把它打成粉碎。」
這位心中充滿愛國狂潮激浪的青年,是來浙江紹興的孫觀漢。前一年七月他剛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工系,旋即考取清華公費,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物理。
清華公費有三年的時間,「那時我只想在美國停留兩年,儘快完成學業,然後束裝回國開座工廠,為國做較實際的服務。」
但由於日本的侵略,砲火襲捲半個中國,使孫觀漢的計劃延擱了九年,抗戰勝利,但就在他辦好護照,想啟程回國,探望闊別已久的老母,共產黨又竊據了大陸,這一阻擋,「我離開大陸已有四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才重返大陸故鄉。」
這位被譽為「中國原子科學之父」的孫觀漢博士,提起這位段往事,心中就充滿了許多激盪,就如黃浦江裡的浪潮一直無法平息。
今年(一九八一)二月底,孫觀漢博士回到自由祖國來,計劃作較長久的居留。
一九三七年,他在戰火中離開大陸,於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回到臺灣,前後有二十二年的別離,從一九五九年到今天他回國,又是一個二十二年,其間他來來回回有十多次,而人生有多少個二十二年?
孫觀漢博士第一次回國,是應當時的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博士的邀請,在清華任教一學年,並擔任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擘畫范氏加速器及原子爐。
今年五月的一個雨天,我們到清華大學拜訪這位譽滿中外的學者,他在核子物理及化學方面,發表了一百三十餘篇的論文,並獲有四十個以上的專利。這是他在科學方面的成就,但他在研究之餘,走到菜園揮鋤之際,也「想想娘家」的事,而寫下一系列的文章,這些文集包括「菜園懷臺雜思」(後改為「關懷與愛心」)、「菜園裡的心痕」、「菜園拾愛」等。
提到他的菜園,這位獲有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化學博士學位的學者表示「種菜是我的嗜好,也是一種非常好的運動,收穫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他頓了一下,右手托著下巴,似乎在回想什麼、沈思什麼。讓我腦海中浮出一位滿面紅光、頭髮變白的老翁,在一片綠油油的菜園中欣賞那大自然所孕育的果實。
「菜園也是讓我想念的地方,而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就是看著生命的成長,我深深體驗到『生長的美麗』(The Beauty of Growth)。」
孫觀漢今年才從美國西屋電子公司退休,他在該公司整整有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八一)的時間,其間自一九五五年起又擔任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室主任的職務,但他在科學領域外又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天空,誠如他所說:「在患難的世界中,我得天獨厚,有一個小小的菜園,在這裡我欣賞自然的純美,洗滌塵世中的庸俗,並試探著企求了解人間的意義。」
他這種菜園中哲學,與他那種誠樸、平實的個性有關係,提到對國內大學生或留學生的看法,他說,以前中山先勸大家「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但「我更進一步希望大家也不要存做大事的念頭」,因為第一、大事不容易做,不是每人能做,第二、大家都只想做大事,小事誰來做?最主要「大家要存心為國家做事可以,盡本分和能力,努力去做。」
在談話中,孫觀漢博士把很多事,透過中美兩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許多比喻,聽起來雖然非常有趣,但仔細一想不禁更佩服他對中國文化特有的見解。
如開車,他說,每次離開臺灣,非常捨不得,但是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那就是每次最後坐計程車到機場,心中鬆一口氣,覺得很幸運,這次在臺北竟沒有被汽車撞傷。
從這一點他看國人的聰明,他說中國人是很聰明,以臺北人這種開車的方式,而每天仍「平安」的回家,何必像美國那種「安全保險」。最後,他不禁也「讚美」國內的開車方法,初到臺北,看見開車之亂,心驚肉跳,但仔細觀察,慢慢的會看到亂中有序。臺北的開車,好像是運動場上的競爭,是很「正常」的事。把運動場競爭的精神,放在日常生活上,也是很「羅曼蒂克」,但我們都忘了,我們競爭的賭注,是人的性命!這種現象是由於只知聰明而不夠智慧!
從這點我們談到中國文化,他說,中國總是說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但其中也有許多壞的文化,說到這裡,孫觀漢博士笑一笑,又提到他的菜園:「一顆好的種子,也要有良好的地氣才能發育良好,這些氣包括土壤、水分、空氣與陽光等等,而就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地氣就是環境,包括社會的習俗和壞的一部分傳統等等。」
所以他認為,國家的問題,不在於「種子」,因為國人的天分、天才都很高,但問題在「地氣」,也就是傳統習俗所造成的腐敗人性,把我們優良的天分,天才淹沒了。
四十多年來孫觀漢博士生活在美國,娶了一位美國太太,他自稱是出嫁了的女兒,中國是他的「娘家」,也因此他特別關心「娘家」,他自己打了一個比喻,「在夫家的客廳,當人們看到我的小腳時,我會跟大家談人類愛美的心理,將自己的小腳和夫家的婦女們穿高跟鞋的腳樣比美,但回到後花園,我會激動的寫信給娘家,抱怨小腳不夠美的感慨。」也由於這種關係,才能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明,有一次他去一所學校演講,帶了一個球,一半是白的,另一半是黑的,他把黑的那一半對著學生,問他們球是什麼顏色,學生都回答是黑的,他說,不對,應該是白的。
若每個人只看一面,就容易自以為是,反之,若能多方面觀察,對事情的看法就會更深入,他說對「娘家」許多問題的關心也未嘗不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來關心它。
這種愛國心,孫觀漢博士認為年輕時,談情是最濃,但持久卻很少,若濃情而不持久,僅能和曇花相比,美是美矣!但於事無補,反而不如「請稍稍的愛我,但請長久的愛我!」還來得實際。讀其文章,更能體驗他這種愛國憂國的心路歷程。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孫觀漢博士代表美國西屋電子公司回大陸一次,也順便探訪闊別四十二年的故鄉──紹興孫端。
孫端在紹興城北十英里,是孫觀漢博士出生的地方,從紹興要坐兩小時的小輪船才可以到達,在返鄉的小輪上,他的一位好友寫了一首詩問他:
不顧曉風寒佇立艙前久
一一細端詳曾是當年否
「曾是當年否?」孫觀漢回憶了一下笑著說:大都沒什麼改變,紹興最有名的紹興酒、紹興師爺、紹興茅坑,「我回去還是都看得到,但那邊還有許多問題,如人性如舊、學校不夠、升大學困難、年輕人拼命想到美國。」
在孫觀漢博士帶領我去參觀當年他在清華大學所策劃裝設的原子爐,屋外正下著雨,他從牆壁上取下一頂斗笠,戴在他那頭髮已發白的頭上,「這傘給你撐,我戴這個」,我們謙辭一陣子,我只好接受他的愛意和關心,在細雨中,一位頭戴斗笠辛勤的「老圃」,平實而詳細的為我解釋他當年如何做……我的心中為他那種「平實而做」的精神所深深感動。
「在國外你整天埋首在實驗室,怎麼還有時間來寫作?而且都是對『娘家』關切入微?」
「我只是把我心中所想到的寫出來而已,有點像年輕時寫愛情信,一鼓作氣,深情傾訴。」據他自己說,在實驗驗室外的「筆墨生涯」,要有靈感、時間與精神來配合。
「靈感經常是來自菜園耕作之時,但要三者齊來,大多數發生在午夜驚醒的時候。」
但我想他的文章所以那麼吸引人,最主要的是,在行文結構中,均充滿對中國的關懷,誠如他自己所言「有心的地方就有愛,有愛的地方就有美。」我們希望他能在「娘家」多住一些時候,以他的愛心更關照些他的「娘家」。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四日台北「時報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