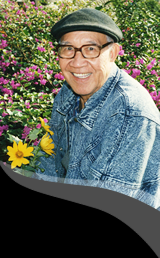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平淡平實
江南
一九七四年仲夏,在香港辦雜誌的某君,邀我陪他去多倫多,中途在匹茲堡停留,順訪慕名已久的孫觀漢先生。
作為孫的客人,停留山城一宵,參觀了「匹大」,還看了那個收藏東方古物甚豐的博物館,然後即登機北上。
我是一九六七年春,到達美國。第二年,美國報紙刊出柏楊先生被捕。得自雙橡園的消息:孫觀漢先生經常用電話找當時的大使周書楷理論,弄得周書楷甚為困擾。
因為孫不眠不休的奔走,呼號、營救,各地的知識份子,紛紛眾志成城,團結在孫的周圍,擁他為當然的領袖,共同從事著一個嚴肅感人的目標──把柏楊先生救出來。
很坦白的說,我和其他朋友們一樣,和這位擅寫諷刺雜文的作家,並無淵源,祇是透過我們共同的朋友顏小姐,略知皮相。甚至,他刊在臺北自立晚報上的專欄,亦鮮少涉獵。原因:來美的前五年,我的絕大部份時間,都分配到英語上了。
不過,憑少數幾個當權派情緒上的喜惡,隨便套一頂帽子,入人於罪,總是件「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
孫先生的感懷,最為強烈。他的道德勇氣,和他超然於黨派,和置身海外的政治環境,都是難得的條件。
有人把他比喻為當年孫中山倫敦蒙難事件中的康德黎,就精神而言,實無分軒輊。
由柏案結的緣,我自願投到孫的麾下,聽其驅策。可以這樣說,假使沒有這根連絡線,我在美國住得再久,也不會認識孫先生的。他搞科學,當時我念近代史,分工細密如美國,越界知名,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說閒話,認為孫借柏楊出名。孫因柏案,在他的職業圈子之外,變得四海皆知,固是事實,但那祇個是個副產品,卻遠非孫的本意。說這種話的人,對孫的人格,和他崇高的品質,母寧是惡意的毀謗。
孫先生大畢業來美留學,早在三○年代,一出校門,即為西屋電器公司羅致,任工程師,其可佩處,是忠心耿耿,貫徹始終,從未萌過異志。
這樣,和西屋的緣分,連帶結下他和匹茲堡的不解之緣。
根據常情,在美國這樣流通的社會,換職業搬場地,家常便飯,反正,那裡待遇好,工作環境好,隨時捲行李走路,入境隨俗,毋足為奇。
孫先生入污泥而不染,他的固執,保守,忠信,淡泊,正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典型。
他住在匹城山坡上的房子,依此地的標準,可以「外觀簡樸,內設陳舊」作形容,絕比不上一個普通鋼鐵工人的家。那天早晨,我們由旅館去他私宅造訪,心底裡的直覺反應,「這像是個『西屋』高級職員住的嗎?」
室內的那架新置的音響,算是比較值錢的東西以外(據說是屬於他唸醫科的兒子的私產)。一切傢私,實在有相當程度的逾齡,依舊退而不休。
胡適和梅貽琦兩位先生題的字,還有柏楊的書法,三者並列,卻是孫先生的至寶,反映其書卷氣。
那天,我們沒有見著孫夫人,夫人回波士頓娘家歸寧。當然,她不中國人,朋友告訴我孫夫人開著朋馳牌汽車,在當地中學教書
孫先生,鄙視物質,重道義,輕金錢,否則,他何以能住在那個平民住宅區,上班工作,下班種菜,而心安理得,一副陶淵明式開門見南山的胸襟心情!
在美國住了四十多年,孫先生不喜開車,遇事找太太兒女出「公差」。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然而,遇到大是大非的問題,他就不放鬆了。
那時候,他和臺灣當道的關係,還十分親近,如果,他老於世故,怎肯為一個素昧平生的文人的冤屈,把個人利害拋卻,昂首闊步去投訴呼籲。
比起胡適之不願為雷震探監這件事,氣節高下立分。
為了出版「柏楊和他的冤獄」那本書,香港的某君藉口投資沒有把握,堅持孫先生付全部印刷成本,孫先生委屈求全,自掏腰包,結果,問世後暢銷一時,那位黑心的文人,連本帶利,都進了自己的銀行戶頭裡去了,老先生一笑置之。
小事糊塗,足堪與愛因斯坦比美。去年(一九七八)夏天,首次回臺,到洛杉磯,發覺訂不到機票,敗興而返,那末,為何不在匹堡預作安排呢?原來,他忘了。
我和孫先生的來往,除了寫信,偶然也通電話,他鄉音不改,那個紹興方言,除非魯迅再世,聽起來,十分吃力。我相信,他的英語,一定也很使他西屋的同事們,大感吃力。但是,正是這些小地方,他使我們對他倍感其可親,可敬和可愛。
對於物理專業,我是門外漢,丟開那方面的成就不說,他的偉大處,正是他帶給我們最平淡平實的地方。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晨於金山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