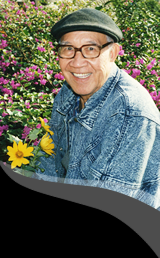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這位仁兄
梁黎劍虹
提起孫觀漢這位仁兄,的確有太多太多令人說不完的長處。初見他,你很可能會覺得他有點玩世不恭,可是他做起事來,卻有一諾千金、鍥而不舍的服務精神,絕不輕諾。我最怕輕諾的人,因為輕諾的人就像庸醫,或像蒙古大夫,害人誤事。而孫觀漢卻是答應了你,就是答應了,絕不誤事害人。我記得他來臺時,我託他在美國替我找一個人,他真的花了不少的電話費、時間、精神,終於替我找到了。
我雖然對他敬愛,可是教我寫文章,本來就是一件難事,尤其在這幾個月內,更是艱難痛楚的事;原因且聽我說來:我從來就沒有寫過文章,雖然我在香港從事出版事業廿年,出版過不少中英文書籍、雜誌,可是我就沒有時間和機會寫文章,因為我有太多的稿件要看,要改,要編排,要校對,和有更多說不出來的事要管、要做,反正我連想也沒想也沒想到要執筆寫文章。在我所能記憶的,祇有為「美國成功的婦女」寫過「編者話」,大約不到一千字。
可是自從患病後,在家養病,出外的時間少,在家的時間多,柏楊先生就鼓勵我改行寫作,經過他的再三又催又促,終於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難產了一篇「憶抗戰,念航空之母」,登在臺北中國時報。隔了六個月,再難產第二篇「女欲養而母不在」,也登在臺北中國時報。同時在香港星島晚報寫了一篇「昨夜夢魂中」,懷念先夫寒操,這三篇難產的文章,我認為對柏楊的好意已有了交待。就不再去費腦筋了。
誰知在今年(一九八○)的春夏間,偶然拿起臺北中華日報出版的「我的另一半」,看完了,忽然我有了也寫一本的興趣。從這開始想下去,加之朋友們經常問及「寒老的詩文專集,何時可以出版?」寒操的文詩與相簿,多到重重疊疊,他逝世已快五年了,我碰都不敢碰它,有時偶然拿起一小點來看,立刻就淚如雨下惹起我無限傷心。這情形,那還有勇氣,有精力來整理他的文件、詩稿。倒不如索性由我寫一本由我倆認識到他逝世止,來紀念他的一生,和酬謝所有愛護寒操的好朋友。於是我就開始擇吉動筆
經過一段艱苦的回憶,回憶時期中經常使我有痛不欲生的感覺,擲筆痛哭的次數自己也記不清楚,我家程嫂每次都用奇異的眼光看我,我祇有告訴她,我在寫有關先生的文章,回想起從前而難過。
在這種痛苦的難產中,我終於想到先寫其中一段「太平洋事變,香港逃亡」來緩衝一下自己的情緒,這樣,我書桌上堆滿了寫過,未寫過的稿紙,整張書桌連插筆的地方都沒有,胸海中也忙亂成一團,正如上元笑我說:像一個從未練跑步的人,忽然就加入馬拉松長跑,其狼狽情形可想而知。
孫觀漢這名字,自從上元十幾歲,模仿柏楊先生筆調,寫了一篇文章寄給柏楊後,不知柏楊用什麼周折,轉到孫觀漢那裡,從此這位柏迷的孫觀漢,也成了梁迷,成到上元迷,以觀漢的愛才和熱情的個性,他倆人立刻成了忘年之交。成了朋友後,觀漢先生待朋友的真誠,細心,慷慨周到,使我這媽媽旁觀者驚奇。到柏楊出事後,觀漢先生十年如一旦地出錢出力,日以繼夜,盡心,盡力,奔走設法援助的場面,能將鐵石人都感動到流下淚來。至於其中細節,在梁上元編的「柏楊和我」中,已有概略報導,這且不必重複!我從那時起,就對這位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的為人,十分敬佩!如此這般,匆匆又過了八、九年,而觀漢對柏楊和上元的友情,那般真誠,八、九年如一日,有增無減,令人十分羨慕。
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柏楊回臺北,我們大家常聚在一起,每次都想念那位從未見面的好人觀漢先生,觀漢自柏楊回臺北後,頻頻來越洋電話,一談就是半小時或四十分鐘,都是閒話家常,沒有幾句是值得在越洋電話上談的。而且有時還居然一天有兩次越洋電話呢。我起身早,有一次我接聽,我就向孫先生說:我知道你不在乎這越洋電話費之昂貴,但也可以留些話在信裡面說明,同時我還著實地勸他回來見老朋友。很高興也很湊巧,他第二天就在電話中決定了回國日期。
於是,我們在臺北的朋友,十分興奮的忙著為他預備住處,和安排如何待這位我所夢想已久的貴人。我也在計劃著如何歡迎他的來臨,於我囑咐廚師老莫,替我到鄉下找乳豬,預備他抵臺的當天晚上,以最隆重的廣東乳豬席來宴請他。提起那小乳豬,真夠我麻煩操心,先得提早三兩天就到鄉下把牠買回來養在家裡,小孔豬卻十分頑皮,一會兒就不知跑到什麼地方,買回家的第二天就不見了,找了好久才把牠找回來。回此我請廚師大師傅,小心把牠關好因為第二天就是孫先生抵臺的一天了,到那天,一早我就問廚師老莫:「小豬呢?」他是最喜歡開玩笑的人,他回答:「今天一早到現在我腳都走痛了,也找不到牠。」我一聽,差點沒有暈倒,我說:「這怎麼得了,我不是吩咐過你好好的看著牠的嗎?」老莫見我生氣了:「好!我再去找,」就跑出去,過了一會笑著回來說:「找到了,找到了。」我才看出來他是和我鬧著玩的。
那一天,除了我,所有人都到機場迎接了,我在家裡也不閒著,一會兒就看看錶,焦急地等著他的駕臨,到了中午十一點多。終於由一大群人,眾星拱月地擁著他進入了我家客廳。
他給的印象是:是一位精幹,聰明智慧高超的中年人,服裝十分隨便,一點也不講究,身材細小,一口紹興師爺的中國話,說起話來慢吞吞。恰巧遇著的全是性急的朋友,弄到他沒有一次能將要說的話說完,雖然大家知道中斷別人的談話是十分不禮貌的,然而大家都像顧不了這些禮節。
當天的晚宴,濟濟一堂,十分熱鬧,坐定之後,他第一道命令要我們不管老少、輩分,都不能稱呼他先生,祇能直呼他觀漢,我們也祇有恭敬不如從命了。第二他立刻將凡是女的,不管老少,全算是他的女朋友,從那一刻開始,他的女朋友數字,逐日增加,情呀,愛呀,這些字不離口,這種風流才子的性格十分表現出他像十六、七歲的大頑童那樣天真,純潔,可愛。就這樣,我們大家圍聚著和他聊天,陪他到處吃小館子,吃他想吃了很久,而吃不著的東西─如燒餅、油條、臭豆腐,或魚蒸肉餅等等。直到他到期要回美國主持那些我們一竅不通的原子、核子,我們才依依話別。
我對孫觀漢,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在科學上的成就,和那些豐功偉業,我且不去談,也不會談。單說他在文學的成就,就夠驚人,以他從小離國在美居往了卅餘年,而仍能寫得一半好文章,好散文,而且是頂瓜瓜的散文,真教我這個生長在國內的土包子慚愧得無地自容。
他聰明才智也不同凡響,當他第二次回臺時,就全變了一個人,更年輕,更漂亮,在言語上更是進步得驚人,說話不獨不比我們慢,而且簡直能迎頭趕上。辯才更是無敵手,記得他回美的前一晚,我們大家公宴他,席上他我要知道他第二天乘的是那家航空公司的飛機?什麼時候起飛等等,從開席後不久大家就開始問他,他不肯說出免得大家麻煩,我們卻堅持要問到底,足足圍攻他兩小時,他卻輕輕鬆鬆地旁顧左右而言他,總使我們問不出所以然來,等到飯店表示要收市了,我們祇有無可奈何地認輸了,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是一個多情種子,大約在數月前我在臺北聯合報看到一篇描述作者和初戀情人再度想逢的文章,寫得細膩多情,柔情萬種,筆調十分像孫觀漢先生,後來果然發現是他用筆名寫的,因此我認為他是一個多情風流才子,是大眾情人,他當之無愧。
一九八○年十月於台北寒盧
摘自星光版「梁寒操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