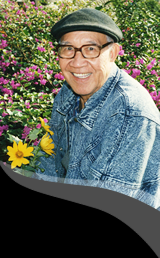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一位校友的歸寧
楊覺民
一九七九年元月九日,孫觀漢先生回到了一別十三年的新竹清華園,他的頭髮幾乎全白了,但精神仍然很好。午餐後幾乎沒有休息,就到梅貽琦紀念館參觀他曾親手擘畫的原子爐,接著又參觀了移動教學反應器及其活動輻射度量實驗室,阿岡反應器,同位素館的放射化學研究室,同位素製造設備,無塵無菌製藥室。他離開反應器區,便到總圖書館參觀,對於原子能資料庫,看得最仔細,並一再垂詢。然後去物理館看了加速器,電子計算機,離子佈植實室,物理系閱覽及低溫物理實驗設備等。再到成功湖畔,先後參觀了學生活動中心,禮堂,學生第一餐廳,第二餐廳,並上山跑到男生宿舍誠齋。在行止間,他對建築物的考究與否,餐具的品質、清潔、菜餚的營養,端詳得十分細心,不時提出批評和建議。大體上說,孫先生認為,今天的清華,較諸十幾年前大不相同了。
當天晚上,孫先生駕臨新東院二十九號作客,東道主人是唐孔筱芳女士,陪客有劉仲凌總務長,曾德霖教授夫婦,錢積彭教授夫婦,及筆者夫婦。唐女士是已故唐明道(一九二七──一九七三)教授的夫人,唐先生生前,多次前往美國西屋公司核能中心進修,都蒙孫先生特別照顧,他對唐氏的讚佩,在他所著「菜園懷臺雜思」(菜園裡的心痕)裡,表露無遺。一九七三年唐先生不幸車禍逝世,孫先生除熱烈響應子女教育基金的勸募外,更不斷寫信安慰遺屬,並請母校妥善照顧。這晚的宴席,是由唐夫人親自掌廚,饌饈色香味均佳。席間女主人曾就臺北報上消息,謂係孫博士願在臺北買新房子,將來退休後回國定居一事,求予證實。他表示無意在臺北置產,但如能有機會重回清華園,他甘願不拿薪水,提供所有時間來和後進他們切磋,只要有房子住就可以了。劉總務長說,房子不會有問題,其他在座的也一致認為,若能得先生榮休後返校,指點引導,必對母校核子科學未來發展,大有裨益。
元月十日晨,孫先生由曾德霖所長及唐夫人陪同,先到梅園向梅校長墓寢獻花,續登十八尖山錢墓,到唐明道教授墓前獻花。回程參觀了核子工程系的放射度量實驗室,電子實驗室,核材料實驗室,中子活化分析室,質譜儀,計算機等。當他看到許多電路板都是學生們自己貼、自己洗、自己銲時,感喟現在是比以前進步了。他說:「十八年前的研究生,要熔鑄一塊石臘,小工不來,他們就只會傻等,不會自己動手。
中午,張明哲校長,及核工系教授曾德霖、陳家威、黃文爵、江祥輝、施純寬,及筆者等,陪同孫先生進餐,飯後由蘇青森陪同參觀了國科會精密儀器中心的光學及電子研究部門。
孫先生這次返校的主要節目,是給大家一次演講,講題是「探鈾新法」。在物理館梯形教室舉行。開講之初,他首先為自己的浙江口音而抱歉,他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紹興人講官話。如果聽不懂我的話,大家不妨想別的事。伽俐略當年能從教當裡掛燈的搖擺、悟出鐘擺週期的大道理,主要是因為那天講道的神父土音太重,他聽不懂,只好對燈出神,想入非非之故。……」
其實孫先生的官話,比起當代的其他浙江名人好懂多了。這回他講的內容是如何利用TLD(ThermalLuminescentDetector熱光偵檢計)法來測定由鈾所放射出來阿爾伐射線劑量,再據以推定其礦藏。TLD是一種化學藥樣,它有一種性能,是在受了輻射後,會使其中的一些電子能量升高而達介穩態,受的輻射愈多,這種電子會愈多。然後若將藥樣加熱至攝氏三百度,介穩能態的電子會受熱而爬高、下跌、發出光子,藉倍光管測這樣得來的發光量,可測前此一段時間內TLD所受的輻射劑量,把TLD滲入泰福隆,切成薄片,使之易於接受阿爾伐輻射劑量,再把這些有TLD的泰福隆薄片布於可能有鈾的礦區,放一個月後,分別加熱測量,推定甚麼地方輻射量最高,然後用脈衝中子產生器,佐以多道分析儀,偵察礦苗分佈的實況,以決定是否值得開採。孫先生曾當場把受過輻射的TLD加熱,使之發光給大家看。演講完畢,不少人發問,孫先生一一作答,並很高興的表示,這比十幾年前講完沒有人敢問問題好多了!最後有位同學問,茫茫大地,該到何處去挖坑佈置TLD,才有希望收穫呢?孫先生說:「這沒有甚麼好辦法,要請教地質學家。他們說那裡有鈾,你頂好聽他的,就像有些病,到了沒辦法時,得請個中醫師一樣。」幸好聽眾裡沒有地質專家,也沒有中醫師,否則一定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怒。
演講後由原子科學研究所初創時代的師生,在百齡堂歡宴孫先生,到會有鄭振華、劉仲凌、曾德霖、楊毓東、葉錫溶、王守益、郎棣、張昭鼎、單越、翁寶山、蘇青森等。宴後由鄭院長陪孫先生返臺北。
孫觀漢先生,浙江紹興人,浙大畢業後,和現任母校校長張明哲,同榜考取清華公費赴美進修。他在匹茲堡大學攻物理,適因抗戰軍興,烽火燒過了大江南北,那時他遠在異域,有家難歸,完成博士學位後,進入西屋電器公司工作。沒想到竟在前人所鄙視的蠻夷之邦,一住四十多年,落戶生根。可是他身在海外,卻心向祖國,所以一九五六年梅故校長在臺籌備復校,登高一呼,孫學長便首先響應歸來,任原子科學研究所所長,目前新竹校園裡大型設施,如范氏加速器及原子爐等,都經他躬親擘畫。
他這次返國,純係私人性質,預計過完農曆春節後返美。筆者以為孫先生對國家的貢獻,遠超過他協助梅校長在臺復校,以及他四十年來在科技方面的成就。因為他對國人、國事的體驗,融會貫通以後,寫成的文章,醒人警世之處,必將書諸竹帛,傳之後世。
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新竹「清華校友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