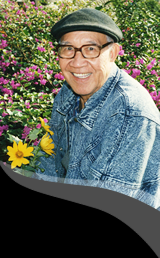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恆毅的人
吳新一
我沒見過孫觀漢先生,但我跟孫先生在過去十多年裡,曾斷續通過許多信,也曾在電話裡談過一次。跟一位真正的偉人,祇要有片面瞬眼接觸的機會,感受一定很深,何況我有緣能跟孫先生書信往返呢!十多年來,或多或少都曾感染到孫先生待人的真摯,以及他不折不撓的恆毅精神。
柏楊,是許多在美國的朋友跟孫先生開始交往的橋樑,沒有「倚夢閒話」「西窗隨筆」,就沒有以後十幾年來如史詩般的孫柏友情,也就浮雕不出孫先生偉大情操。
一九六二年的暑假,我在紐約打工,住在一位東海大學同學的公寓裡,在那兒我第一次接觸到柏楊的雜文「怪馬集」。在以後的六年裡,斷續的讀過不少柏楊的雜文作品,常常每隔數月就重溫故夢一次。一九六八年的暑假,我接到一位在芝加哥同學的信,他告訴我,柏楊已因文字闖禍,被捕入獄,並問我能否為柏楊案件寫點東西,讓許多愛好柏著的柏迷,都能知道他們所敬愛的「糟老頭」,已為自己所信仰的原則──寫作自由,而闖了大禍,並且希望愛好柏著的讀者,能夠上書當局,群策群力來營救無助的作家,俾使他能早日脫離苦難,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跟匹茲堡的孫先生聯繫。我因深喜柏作,並且熱衷於美國的真民主,真自由,深感我自己生長的祖國,要是能百尺竿頭再求進步,因此欣然接受了這份差事,這是我和孫先生交往之始。
那年秋天,在我寫「親愛的旅美朋友們」期間,孫先生寄給我長達百餘頁的資料,有起訴書,答辯書,孫先生上書當局的副本,以柏楊家屬寫給孫先生的信,讓我能寫篇有憑有據的文字。在那期間,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收到孫先生的信以及陸續補齊的資料,讓偏處僻壤的我,能有足夠的第一手資料,來從事科學研究式之工作。孫先生每封信都有許多感謝的詞句,好像是我在為他本人作什麼了不起的事似的,真使我汗顏不已。孫先生的信多半是在午夜夢迴,清晨時寫的,有時長達五、六頁。初稿定後寄給他看,孫先生又不憚其煩的仔細反覆更改,使得文字讀來,有如報述新聞一般,儘量減少主觀的詞句,他把稿件及他的意見寄還給我,如是暫有四、五次之多,直到那年年底,才算定稿。
我們都知道孫先生是極為忙碌的科學工作者,不是以寫作為生的人,在他五十歲以前,好像除了科學論作外,沒寫過其他的文章,但跟柏楊結上文字交後,曾花了不少精力來編「柏楊語錄」,寫了許多有深度思考的文字,在臺灣報章上發表,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集在「菜園懷臺雜思」(關懷與愛心)中。為了柏楊的苦難,他寫了許多信給在臺灣有影響力的朋友,又因為他這種出力不討好、書生論政的精神,各方面對響應營救柏楊都極為熱烈。這些文字他後來又花了許多精神,收集在他所編輯,而在香港出版的「柏楊和他的冤獄」裡。
從孫先生的文章上,可以看出孫先生寫作時,並不像柏楊那樣有如天馬行空,信筆一揮,就成順暢可讀的文字,而是點滴砌成。從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都可以感覺得出來是孫先生再三斟酌後才下筆的。孫先生的文章,有如科學研究者的論作,寫時嚴謹認真,看的時候也很費勁。由於孫先生寫的東西都言之有物,反覆論理,讓讀者看過後,有如上了一堂課似的感覺。如果精神不濟,一目十行的流覽一遍,那麼就會像在課堂上打了瞌睡那般,看完之後仍不知所云,非得從頭來過;句句咀嚼,才能領會到孫先生苦口婆心的深意。
在柏楊入獄的九年多期間,一般柏迷對柏楊聲援的熱情,從激動而漸趨平淡。在他出獄前一、兩年,除了「南北極」上偶有「郭衣洞」的諷諫文字,可以找出柏楊的影子外,差不多已看不到有關柏楊旳消息或文字。但孫先生對柏楊的熱情,並沒有因時間而沖淡,也沒因他所作的努力沒得到預期的效果而氣餒。我記得在一九七五年的秋天,我到匹茲堡去參加一個會議,由於事先沒有跟孫先生聯繫,臨時在那邊打電話沒能找到孫先生,回來後寫信給孫先生,順便提起我曾去過匹茲堡,他覆信說很遺憾我們沒能見著,不然可以藉著見面的機會,交換一下援助柏楊先生的意見。
一九七八年元月二日,我藉著離開臺灣十六年第一次回國省親的機會,在寒霧家裡見到風采勝人的柏楊先生,那天我們談了三個多鐘頭,提到大家都沒見過的孫先生時,心裡都有說不出的溫暖感覺,正如史紫忱先生所說,孫先生在我們的心目中是「神」,而不是眾多研究科學傑出學者之一。我很高興的聽到孫先生終能回到臺灣和柏楊相聚十七天,讓一個有如史詩般的友情,有一個完美的結局。見到柏楊先生是我平生最大的榮幸,能和一位現代的民間哲人作一席談,親身領會到他銳利的觀察力以及清晰超人的分析,真是終生受益匪淺。我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見到孫先生,感受到「神」的溫暖和「太陽」(Sun)的輻射熱。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寫於 德州理工大學中國同學會座談會後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