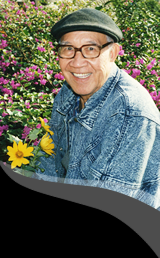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一種啟示
陳 文
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底的事。我在給朋友倪君的信裡,為柏楊入獄的事感到悲痛。倪君告訴我他把那封信轉給孫觀漢了。當時我不知道孫觀漢是誰,因為我是一個沒有科學細胞的人,對科學家的名字一向不注意。不過當倪君告訴我孫觀漢是個舉世聞名的物理學家之後,我對這位物理學家和人道主義者的結合體,感到十分好奇和敬仰。過一兩天,孫觀漢的信來了。他立刻把我當做他拯救柏楊孤獨無援道路上的一支生力軍。我們的友誼,因此展開。
每次看孫觀漢的信和文章,我都會激動得流淚。他寫文不像他所最佩服的柏楊那麼鋒利精闢,而是有條不紊的平舖直敘。他不用繁華詞藻的堆砌去求文字表面的美,但是字裡行間,充滿著貫穿讀者心懷的誠心與忍耐力。使讀者在佩服他高超的智慧之外,更被他的愛心所震撼。這個智慧和愛心是他人格的寫照,也正是他寫文的獨特風格。
孫觀漢的愛心和忍耐力,給予我很大的啟示。每當我因柏楊出獄的遙遙無期,感到灰心失望而欲罷休的時刻,看看孫觀漢的信,就覺平心靜氣得多。記得有一次他說:「我感佩妳的熱誠、愛心,和它們背後對人道的貢獻。但是人也間無形的殘酷浩劫,可能會衝擊著這種熱誠和愛心的發揮。愛是最美的事,但是要點點滴滴,細細長長的愛,而不要濃而猛的愛。」對於如何愛中國,他對我說過不只一次:「中國的事,一言難盡,也是一言可盡。近一、二百年來中國不振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有一個大敵。這個大敵不是外患、軍閥,和專制政權等,而是柏楊所謂的醬缸。這個敵人在那兒?我們不用遠看,只在妳我身上和心中一看就知了。」他也常說:「所以我不喊打倒誰,因為我還得想法子處理我心中的醬缸。對於我們的國家──大陸和臺灣,我們不應責難太深。最好採用一種Loyal Opposition的態度。他們好的,我們頌揚;惡的,我們誠意的苦諫 。」
初聽這話,我雖服氣,卻認為這老先生血氣衰了。但是經過幾年來細心的咀嚼,體會到這是多麼勇於認錯,和以身作則的見解!而多年來我所尋找的東西,竟都在這短短的幾句話裡了。
究竟這些年我在尋找什麼呢?這要追溯到我的小學時代。我從七、八歲時就喜歡寫文,後來經過中學而到大學,總希望把腦子裏幕幕起伏不定的悲憤思潮寫下來,並夢想將來做個記者或辦份雜誌。但是當時幾個報人的下場對我很沒有報鼓勵,而我那種與當時一般名作家不同的思想,也使我懷疑自己的不正而不敢落筆。來美後,見慣了思想與眾不同的人和文章,對自己略有信心,也就不免躍躍欲寫。但是每提起筆,就覺熱血沸騰,下筆如衝鋒陷陣般猛烈。於是又開始對自己懼怕起來,懷疑文章裡還缺乏什麼,而不肯投寄出去。
多年來,人生的教訓使我能日深月深地領悟孫觀漢的啟示。我體會到一個中國文人若想發揮他以文諫政的靈感和召喚,除了他的一枝銳利的筆以外,還必須先學做聖人。中國的醬缸太大,醬氣太濃。如果不能先建立一個努力驅除自身醬氣的胸懷,就不能了解和同情他人的醬味。如果我不能同情他人的醬味,那就必須得準備以生命去迎接那些被醬味薰黑的人的面子問題。我想起孫觀漢曾在一封寫給一位朋友而那位朋友並沒見到的信裡這麼說過:「打敗擁護醬缸的人群是治標,而打倒醬缸才是治本。治標的本錢是權、錢,和槍;治本的本錢是智慧和愛心。中國人若只憑勇氣和智慧去和擁有權錢槍的人們一爭長短,去衝鋒治標,可能會因著急於治標,反而使國家失落治本的智慧了。」如果那位朋友今天見到這封信,可能也會同意他這種語重心長的說法吧!
孩提時代寫作的夢,摸索到今天,尚沒有真正寫下第一頁。如今柏楊、孫觀漢的智慧、勇氣、毅力、犧牲和愛心,為我奠定了一個方針,而從柏楊的起、落、又再起,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也許我可以打開白紙本兒,毫不悲憤的開始寫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於美國
摘自星光版「菜園拾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