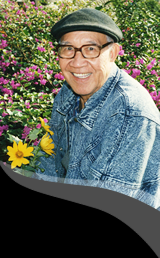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菜園裡的愛
陳麗真
一鼓作氣看完孫觀漢先生「菜園懷臺雜思」之後,心裡有無限的感觸,這些感觸使我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不管我的想法是對還是不對,它總是從我內心誠懇的發出來的。
雖然我不能親眼看到孫先生寫「雜思」時的情景,但是從他的字裡行間,我體會到他是多麼真誠的,熱衷的坐在他的書桌上寫作,如同他每次在菜園裡一樣。在「雜思」裡,有孫先生真摯的愛;他愛他的兒女,愛他的母親,愛他的家,愛他的國,每當想到這個被他所深愛的祖國在許多地方尚是那麼不如人意時,他有著無比沈痛的嘆息。正如我們在自己的「家」裡,每天看到這個家始終亂七八糟,嘴裡喊著「整頓」「改革」,而實際上還是「髒」與「亂」一樣,我們也有我的苦悶,這苦悶也來自「愛」。
雖然方式不同,想法不同,但是我們對祖國的愛則一,我們希望早日完成國家的強大,我們希望挺得起胸膛,抬得起頭,我們希望在國際之間的友誼集會上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可是這一切都得有本錢,有被人尊敬的本錢,有值得自傲的本錢。然而,只要我們稍為深入的對我們自己的「家」有比較深一點的瞭解,那麼正如孫先生所說的,我們便感到慚愧,甚至有一種不可原諒的羞辱感。我們並不是不原諒我們的祖先,並不是不原諒我們的政府,而是不原諒我們自己。
在孫先生「尊重事實」一文裡,他說:「柏楊先生更沈痛的說過,在西方,知識是權力在東方,權力是知識。」這是一個人受過多少慘痛遭遇之後,才能體會出來的一句話,當他老人家說出這一句話的背面,誰曉得他曾經歷幾許的滄桑?因為有許多人爭取「事」的目的,不是為「大我」,(當然也有例外,不過看起來這例外是越來越少),而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因為我們這個「家」裡,權力代表一切,他不但成了一個大學問家,很可能的,一個有了相當「權力」的人就會被認為是個「神聖」,這都是有傷我們進步的一大阻力。不幸的是,直到目前為止,這「阻力」好像還是很大。所以孫先生又說:大學生的惡習,是愛著整個社會的陶冶而發生的。我很同意狄仁華先生的看法,缺乏公德心,或擴而言之,缺乏良好的習俗,對中國的革命和建國,是一個很大的障礙,無論從政者如何忠心和英明,誰能敵得過如來佛掌那樣大的醬缸?中國歷年的貪官污吏,多得可怕,但誰又知道多少清廉忠貞的從政者,被那些巨大可怕的惡勢力埋葬了!
「柏楊先生給我的信中,有一段很動人而痛心的話說:『伊藤傅文回到日本能使日本強。辜鴻銘回國,只能教書。非中國人不行也,而是醬缸太深太濃,人才都被醬死。』到現在大家該深深的覺得,中國的困難問題中心,是在整個社會集體的人性……」。當然,要改變整個社會,困難重重,因為社會中心是人,要把社會的習性改好,就得先從沒有好習性的「人」改起,反顧一下目前我們社會上的現象,說句大膽的話,大家只知道懵懵懂懂的過日子,只知道一昧的尋求物質的享受,只知道有己而不知有人。狄仁華先生所說的中國人缺乏公德心,就為了大家只為自己著想,從不肯約束自己。
因此不守法認為沒啥了不起,貪污只是小意思,出售美國人救濟窮人的『顧念包』還向國人大吹是『洋貨』呢!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品格問題,和靈性問題,這道德、品格和靈性,同學問沒有關係,當學問好的如孫先生,如柏楊先生等等的人的道德、品格、靈性,是很高尚的,但這是比較特殊的人物,我說的是一般的自認為也是學問很好的人,不一定道德、品格都好。相反的,有很多並沒有什麼學問的人,其道德,品格照樣高尚無比。所以學校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中國人似乎忽略了家庭的品德教育,而所有為人父母者,是否把眼光放遠了?在苦心孤詣的培植下一代呢?這又是一個頗耐人深思的問題了。
「雜思」上,孫觀漢先生為了他朋友唐明道先生寫給他的信裡的幾句話,而心中激盪了好幾天,唐先生說:「為什麼同一個人在國內的時候,不願吃苦,不守秩序,可是只要飛到太平洋的彼岸,馬上什麼事都願意做了,洗碗除草都行,交通秩序也很懂了。」是中國人天生的賤骨頭嗎?是中國人在中國就靈竅不通嗎?推其原因,是中國不守法的人太多了,再多一個不守法的人又有何妨呢?既然大家都不守法,那麼大家就都談不到羞恥,更無須去考慮有否傷了自尊的問題了。就拿臺北市等候公車的排隊情形來說,如果每個人都能規規矩矩的照先後的秩序,我相信就不會有人敢捷足先登。蓋守法的人多了,不守法的人自然膽怯,即使不膽怯,他也要考慮考慮他的尊嚴。英國人從小就不斷的培養每個人的自尊,因為自尊使人守法,因為自尊使一個人不得不努力的去學習做人、處事,可是這裡面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自尊?有錢有勢有地位就有自尊?沒有高樓大廈,沒有顯赫地位就沒有自尊?孫先生在「洗碗的精神和勇氣」一節裡說:「首先我們先得瞭解,凡是做對人和對自己有益的事,都是上等事,都是人做的事。不但洗碗,即使洗馬桶,也一無羞恥可言。但我們的留學生,口中雖念著同的經,心中卻流著強烈的『傷心淚』,這種矛盾,這種口是心非,關在象牙之塔裡的現象,社會上極為普遍。大家在口頭上崇拜中國傳統的美德,行動上卻完全相反。這正是三百年來中國文化破產最顯著的病根,也是我們民族墮落的原因。一洗碗有傷自尊,是留學生的一個例子。
現在反顧一下「家」裡的人,貪污好像不算有傷自尊,而出賣勞力如做工友、做下女,反而是一種有傷自尊的工作似的。在公共場所,如二、三流之飯館裡,高聲談笑,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現象,為什麼每個非扯開嗓門大嚷不可?正如孫先生所說的,這是習性的問題,這問題如果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二、三流(不要說一流了)的館子裡,也一定自然消失,因為人家都是鴉雀無聲的,看你一個好意思嚷吧!類似這種小問題,在「家」可以說俯拾即是,問題雖小,影響卻大,反瞻一下目前這種不上軌道的社會風氣,誰說不是由於這些「小」問題雖小,影響卻大,反瞻一下目前這種不上軌道的社會風氣,誰說不是由於這些「小」問題累積而來的?所以孫先生忍痛的離開了他所深愛的祖國,縱然他有許多其他冠冕的藉口,但是他說:「真正的理由藏在我的心底,我覺得我太懦弱,我不夠堅強,我敵不過那種我認為不好的習俗!如果說是不愛祖國,我還有什麼好辯!」看到孫先生這幾句話,我心裡很難過,如果不是我自作聰明的話,我相信孫先生說這幾句話時的心情一定非常沈重,好像一個忠心的孩子正準備盡其全力來整頓自己的家,而家人卻無法容納他一樣,他只好落寞的離家出走。好在愛國不一定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如孫先生說:「只要我們替祖國保持一種愛國和建國的元氣,並且在國外能把這種愛祖國情緒培養和發展起來,這也可以說一種失而復得的收獲。」很多出國的留學生或華僑都比在自己國度裡更懷念祖國,更熱愛祖國,這是一個不能抹殺的事實,只要這個事實存在,那我們對海外學者的遲遲未歸,似乎不應再去忍心苛責。關於這一節,在孫先生的大作裡,有很詳盡而貼切的分析。
在「雜思」裡,我另外要提的是附錄部分──寒霧小姐寫給柏楊先生的兩封信,寒霧小姐文筆之流暢,詞句之優美,吐字之幽默,及分析事理之簡潔而有深度,絕非出自一位十六歲少女孩子口中,而她竟真的只有十六歲,這真是一個天才,願這個天才保有她那份「持久的愛」,並且「下定決心」,和已經不「十分迷惘」才行。
一九七八年三月於台北
摘自星光版「陳麗真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