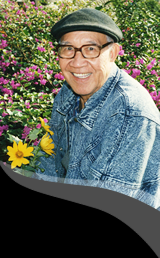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菜園懷台
朱文長
甚麼時候第一次認識孫觀漢先生,已經毫無印象了。這大概是因為孫先生淡無奇的作風所致。說老實話,要不是因為孫先生是名人,我想很少人會在表面上看出孫先生是位奇人的。他既不年輕,又不「漂亮」(雖然十分端正),又一口紹興腔的英語,一點不像在美國住了三十多年的人,穿的衣服,也離風流瀟灑遠得很;雖然他有一位年輕美麗,賢淑而又聰慧絕倫的美國太太──勞娜夫人。
第一次真正對孫先生有印象,是在一次歡迎凌鴻勛先生的晚宴後,閒談時同座某君強調人生應以弄錢為最高目的時,孫生先插口說:「人生還是應該以做點事業為目的。」這在金元國家裡是如燠熱中颳來的一陣涼風,使人在沉睡中突然清醒。
以後有許多事使我發現孫先生是一位熱愛中國,熱愛民主,熱愛進步,同時也十分勇敢,十分負責,十分實事求是的人。
匹茲堡有一位年輕教授,跟著一些所謂「自由主義者」的「中國專家」後面發表一些不負責任、莫名奇妙的言論,諸如:「金門、馬祖應當交給中共」之類。孫觀漢先生與匹茲堡大學李景均教授就聯名在當地報紙上給那位年輕人寫了一對措詞委婉而十分嚴正的信,責備他甚麼權力問也不問金門、馬祖當地人的意見,就把金門、馬祖送給中共?那位教授竟始終未能答覆,也未曾道歉。這就是美國一般所謂「自由主義者」「中國專家的」的通病。所知不深,所以所論不當。滿口自由而實際上是落入帝國主義者宰割人群的窠臼。孫、李兩位先生的正義感將這些假自由主義者的面目揭穿,是十分可佩的。
當我代表東方雜誌編者金耀基兄請求孫先生為東方撰稿時,孫先生謙辭,說他多年不用中文寫作,寫來十分吃力。而且僅餘的一點寫作中文時間,也已經許給臺北自立晚報了。一方面他薦賢自代,一方面說不久要送我一本小書。
果然,小書寄來了,是他寫的「菜園懷臺雜思」。拿來一氣讀完,覺得是一本很難得,以至性至情而又非常流利生動的筆法寫的時代心聲。
如果還有人不知道孫觀漢先生是誰,我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他的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Company)研究中心原子能部門的負責人。發明並獲有四十多種專利權,發表了近一百篇的科學論文,曾協助梅月涵(貽琦)校長建立清華研究院原子爐,而被時代雜誌稱為:「給月亮照上新光的太陽。」(The Sun who casts new light on the Moon)這是一句語意雙關的俏皮話。因"為孫先生的英文姓是Sun,意為太陽。(見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八日美國時代雜誌Time科學欄。)
這樣一位成功人物,在普通的情形下,是可以不寫這本小書的。但是一種愛中國,愛人民的至誠,引導他寫了這本「菜園懷臺雜思」。
在他的序言裡,他將在海外的中國人比作出了嫁的女兒,而他自己的心情是:
在夫家的客廳裡,當人們看到了我的小腳時,我可能會跟大家談談人類愛「美」的心理哲學和演變,並且將我的小腳和夫家婦女們因穿高跟鞋而變形的腳樣,互相比美。但當我回到後花園寫信給娘家……時,我難免要激動的說些小腳不夠美的閒話和感慨。
對於一些要求所有在外的人回國來的,他說:
出嫁女兒愛家的心情,有時不一定比在家的女兒淺。當娘家的姊妹們有時擦粉擦得濃淡不勻時,出嫁的女兒寄面鏡子回來,也不是完全不合人情吧?……我們還希望娘家的人們,看到我們從外面寄回的鏡子,有所警惕,使將來的姊妹兄弟們,當他們懷念老家時,他們的老家,不再是「下雨即漏」,而是「溫暖融樂」的真正天堂。
這種心情是多麼真摯啊!
統觀全書,其中精采的警句非常之多,隨意摘來,如:
無論中西,好話總是到人去了才說!從夢麟先生的過去,我們應得一個教訓,我們不要等人去了才說我們佩服他、敬仰他。
因此他除了寫「泣念蔣夢麟先生」「清華和酒」(紀念梅月涵校長),「一位在做中成功的政治家」(紀念陳辭修)之外,又用至情寫了:「遙遠的致意」和「懷念和感想」,來讚譽一位素未識面的「土生老頭」柏楊先生。使柏楊先生:「接信後反覆閱讀,和老妻面面相對,熱淚互流。」如果不是至情至性,如何能使那冷嘲熱諷罵慣了的老作家,如此感動而覺得「值得為他『寫斷手』」?
直接的結果是柏楊先生寫成了「魚雁集」。如果沒有孫先生的讚許,這本十分精彩的書也許就不會有了。
孫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的毛病,有一針見血的批評,那就是虛偽、欺騙。他說:
在國外住久了,一旦回國,幼司空見慣的東西,在腦中卻產生新的印象和估價!譬如:臺北的商店,都有傳統的招牌,上書「不二價」「童叟無欺」……。用科學方法去衡量臺北這些招牌,往往使人內心感到一種厭惡。……因此我每次都很激動,覺得這些招牌應該丟到毛廁裡去。其實招牌上的話,何嘗有錯?所錯的是:(一)商人不該用這種冠冕堂皇引人的話來做欺騙的工具;(二)社會上缺少一種根據事實去辨別是非善惡,衡量事物的風氣。
其實欺人的豈止是商人?士大夫也是一樣。他舉了個例子:孔子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西方的學習沒有讀過,卻在拚命的實行,可是中國學者卻常在不知的時候,仍厚著臉勉強說「知」。孫先生一方面責備這些人,但另一方面卻更進一層指出中國更嚴重的毛病是:「社會上已養成一種不顧事實,不求客觀,不用標準來衡量的習慣。」他說:
記得七年前,在國內某大學短期教書和做事時,我忘了國內的習俗,時常說:這個不知道,那個不知道。有一位對我不友善的同事就不客氣地罵我說:「你甚麼都知道,做甚麼大學教授?」雖然他應該明白,求學愈多,不知道的更多。但他那麼一說,使我對孔子說過和西方教育教我的:「不知為不知」的那種精神和信仰,幾乎受到沉重的打擊。
他的結論是:
話是孔子說的,事實上西方人做到了,我們用不著把孔子丟進毛廁……讓我們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平心靜氣來衡量事實,衡量後選好的做──不論中或西。
可是要養成一種新風氣談何容易?孫先生在「尊重事實」一文裡說:
去年我在青雲開的一個舖子裡買過一雙鞋,今年破了,又到原舖去照樣的買一雙。一個胖伙計拿出一雙鞋來,那鞋頭又尖又淺,我將一只舊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櫃上說道:「這不一樣……」「一樣,沒有錯。」「這……」「一樣,你瞧!」我於是買了尖頭鞋走了。
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魯迅買鞋的故事。去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回到祖國,在臺北要給內人勞娜買一件錦繡的短上衣。從美國帶了一件舊衣當樣子。衡陽街那爿店中根本沒有類似的上衣,但是那位店員拿出幾件衣服來,很認真地堅持他的衣服尺寸和我帶去的衣服是「一樣」!
這兩件事,一件發生在北平(?)一件發生在臺北,事情相隔約四十年!雖然地點和時間大異,可是情形卻幾乎完全相同,我們可以推想這種藐視事實心理的根深和普遍!
這不是我們在中國社會中天天遭遇到的嗎?孫先生認為不應總歸罪於從政者的不良,他說:「整個社會和整個人性的不良,比任何因素來得都大。」他覺得,「社會是個人組織而成的,當我們分析和指責整個社會時,我們不能忘了屬於我們自己的一部分責任,我們責人之後或之前,更應自責。同時我們應該知道世界上最有效的事,是從自身自心做起。」
是的,如果從今天起,每一個尊重事實,則中國的現代化當可快速得多。
可是改變社會風氣又談何容易?孫先生描述他自己的經驗:
我很愛臺灣農民所戴的三角形的竹笠帽,又美又廉又實用。有一次戴了竹笠帽在學校迎候從臺北來的幾位要人,因為帽子的關係,幾乎使那幾位要人找不到觀迎他們的主人。因此這樣美而廉的祖國的產品,我只好帶回到美國來欣賞了。
記得初到臺灣時,每當出外辦事遇到吃飯的時候,總是邀著(實際上不是邀著而是強拖著)司機一塊兒,後來慢慢地不十分公開這樣做,只好「偷偷」地做,到後來連偷偷地也少做了!
我閉上眼一想,孫先生的司機坐在飯桌上的不安,和同桌其他客人們(自然也得看是誰)的不平,不禁啞然笑了。我們的社會畢竟基本上還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儒家社會呀!
在孫先生的眼裡,勞工是真正神聖的:
在小的時候,家裡沒有傭人,燒菜、煮飯、洗衣、打掃等都母親做。……每次假期從杭州回家,尤其是冬天,常搶著母親的菜籃和簸箕去積有冰塊的河旁淘米洗菜。做那些事,當時不覺得苦,現在回想起來,更是甜蜜。但是……鄰居以及所謂「有知識」的同學們,常用譏笑和同情的口吻說:「當了大學生,還做這些事」!……為甚麼我們產生這樣一個環境,使一個大學生做些代母勞手的小事而感羞恥?
這些對傭人們不滿的批評,不論好壞,都是從「主子」的立場來看。同時我們都忘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大家都是人,為甚麼要人家替我們做奴役?
這些話對我們這一代的人真是鞭辟入裡!我們這一代幼年時看過侯家三老太毒打丫頭,看過王家大老爺「來人啊」一呼百諾的威風;自己也許還過過「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少爺生活。但另一方面也看見過一隊隊知識份子被送去勞動改造,替人做牛馬。這種活生生的教訓應該足夠教育我們了!這世界不應當是一個人奴役人的世界。「彼亦人子也,當善遇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是早有聖賢說過了嗎?可是為甚麼東方社會裡連許多自己能料理的事都不屑動手呢?孫先生在他的「洗碗的勇氣和精神」一文中,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刺目而又扎心的問題:
為甚麼同一個人在國內的時候,不願吃苦,不守秩序,可是只要飛到太平洋的彼岸,馬上甚麼事都願意做了,洗碗除草都行,交通秩序也都很懂了?
孫先生回答這問題說:
首先我們先得了解,凡是做人和對自己有益的事,都是上等事,都是人做的事。不但洗碗,即使洗馬桶,也一無恥可言。
他進而指責那些口中唸著勞工神聖,而心中為勞動而傷心的人:這正是三百年來中國文化破產最顯著的病根,也是我們民族墮落的原因。這種口是心非,不尊重事實的習俗,正是我們的敵人。
這使我想到有一次和于斌總主教談到輔仁大學鼓勵工讀生打掃校舍的情形,這在美國是常事,幾乎可以說是教育的一部分。于總主教卻說因為學生做的工太不夠標準,只好另請職工、工友代做了。我聽了悵然者久之。這一方面固然反映國內工資太低,但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不願好好做的情緒在內呢?
在「船到橋頭自然直」一文裡,孫先生對國人做事沒有計劃和只顧自己的自私心,有極深刻的批評。
孫先生這本書不但表現出他是一位熱愛中國的志士,也表現出他文學上的天才。在「母親!母親!」一文中,他寫道:
昨天穿著母親親手做和補過的布鞋;今天卻看小女兒半新和昂貴的皮鞋被拋棄!
昨天在孫端河旁用木桶替母親掙扎提水;今天在實驗室中夢想利用巨大的核子熔合能。
昨天扶著小腳的母親,去杭州廟中燒香,用紹興話向菩薩祈禱;今天小女兒拉著我去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馬戲,並且用著臺灣社交上認為最時髦的英語,和猴子交談!……
這是多麼當於詩意和哲理的文章啊!難怪柏楊先生說:「嗚呼,真是上帝的恩典,教他去研究原子、核子,如果也教他從事文字生涯,真要把柏楊先生擠得上吊。」
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臺北「東方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