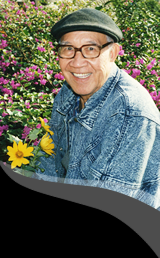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我所認識的孫觀漢先生
鄭振華
我從沒有一點寫作經驗,也許我可以編出許多理由來說明為什麼,但主要的原因是性懶、筆拙。平時我工作確實很忙,但孫觀漢先生一定不會比我少忙一點,可是他卻寫了許多文章,不但在國內發表,有時為了使國外人士對共產黨有正確的認識,亦在國外發表。所以一個「懶」字我實在是無法推托;當孫先生出版這本大著的時候,囑我寫序,理應有很多可以寫的,但寫寫塗塗,費了好多天,還是不能繳卷,不是筆拙是什麼?在另一方面,由我自己的經驗,看一本書的時候,往往希望對作者多了解一點,諸如他做些什麼事?有何成就?以至於他的個性、為人及家庭如何等等,因為這樣可對他所寫的能更深切體會。對孫先生,在這方面我多少知道一點,因此願就這方面作一報導,以求增進讀者對孫先生的瞭解,因此而能體味到他寫作時的心情,進而領會他的心意。
孫觀漢先生是浙江紹興人,生於一九一四年六月,童年在家鄉度過,一九三六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化工系,旋即獲得清華獎金赴美深造,就讀於賓州匹茲堡大學,一九三八年獲碩士學位,一九四○年獲博士學位。他並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卡耐基工學院及羅吉斯脫大學研究。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六年任柯達公司化學研究員,一九四六年起進西屋公司為物理研究員。迄今二十餘年,從事於核子物理及化學方面的研究,發表論文一百三十餘篇,並有四十個以上的專利(美國),自一九五五年起,除了研究工作之外,並任西屋公司放射線與核子研究所所長之職,負責有關的研究及其行政管理。在教學方面,於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年,曾在匹茲堡大學兼任教授,並指導研究。一九五九年應梅貽琦校長的邀請返臺,在清華任教一學年,並負責原子科學研究所所務。其後又應陳可忠校長之聘,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返清華各二個月,指導研究。此外比較短期的,於一九六○年曾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聘請,為核子科學方面的顧問,來臺協助計劃核子科學的研究發展。一九六一年曾返臺參加陽明山第二次會談,一九六五年則為西屋公司在臺設廠事宜來臺考察二週。此外又曾於一九六○年、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四年,擔任中國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置常會代表團顧問。一九六四也曾為中國參加國際文教組織在澳洲召集的會議代表團顧問,對中國代表權及其他有關中國權益的各項問題,都有很多頁獻。
孫先生的研究工作極有成就,例如他曾發展了很多種新的光學玻璃,他是第一人用「閃爍計數計」測定中子,也是第一人測定鈾及釷的快中子分裂所產生的遲發中子,等等不勝枚舉。但為了對一般讀者說明得更具體一點,下面我舉二件他較近年的成就:
一、放射性元素的蛻變率與光速一樣,是公認不變的,雖然早在半個世紀前科學家即開始從事放射性元素的研究,也曾有許多科學家設法用溫度、壓力及電磯等嘗試控制放射性的蛻變率,但都沒有成功。孫先生於一九六四年六月用鐵的同位素,第一次完成了這一項傑出的實驗,他使其放射線蛻變的表視半生期延長了。(參考美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及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九日臺北中央日報。該雜誌稱:此一發現為核子物理領域展開新的一頁。)
二、月球只反射太陽光而其本身並不發光,也是多少年來一致公認的,但孫先生於一九六六年十月發表他的理論,即:散佈在月球表面的隕石粒子,被宇宙線中的質子打繫後,當溫度在華氏二百五十度以上時即發光。但太陽照不到的陰面,因溫度太低約為華氏零下二百四十度左右,則不但不發光,反將其能量吸收。因此當月球陰的一面轉向太陽時,溫度很快升高,於是在月球的陰陽交界面約有一百六十公里寬的區域,月球本身是能發光的。他並在實驗室裡以模擬月球表面溫度變化的狀態,證明了隕石粒子的發光,這是一項非常重大的發現。(參考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時代雜誌及臺北聯合報譯文)。
由於他的成就,在一九四八年曾獲得美國陶瓷學會的梅耶獎,一九六○年則獲得在美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工程獎。
我和孫先生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五九年一月,梅貽琦校長召集有關反應器建造工程的一項會議席上,其後因工作關係,見面機會較多,但第一次他在清華任教的十個月,我卻有七個月不在國內,一九五九年以後孫先生雖曾多次來臺,但為時都比較短,我們常在一起的機,在相知的八年之中,加起來不過八個月。雖然會短離長,但我們建立了深厚友誼,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套一句孫先生自己的話,他愛「娘家」,我更愛我家。有了共同所愛的家,即使有時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意見不同,過一天也許我會告訴他說,某事某事因我沒有看到另一個角度而錯了;也許他會告訴我說,某事某事因他對國內情形隔閡而未能充分瞭解。總之,一切都是基於;希望能為自己的家做些事,希望自己的家一天比一天好。(對於「既愛自己的家,就都該回來待在家裡」的說法,我覺得有一點像要求我們手指頭都長得一律一樣,整齊劃一是整齊劃一了,但對手的功能未必是最有效的。)
孫先生已結婚多年,有二子(十九及十六歲),來臺時還是二個放鞭炮的小孩,今年已將大學和高中畢業,還有一個小女孩(七歲)。孫太太勞娜,我比較不太熟,因為見面的機會較少,但知道她做得一手好且菜,而且非常賢淑,中文也學得很好。在日常生活上,孫先生是非常樸實無華的。他喜歡喝一點酒,但什麼酒都可以,尤其喜歡高粱及五加皮,吸煙也是如此。飲食方面尤為隨便,喜小吃,在沒有發現漢中街一家小吃店有臭豆腐干前,就曾在新公園攤上吃,也喜歡嗑瓜子和吃大眾化的油條大餅和豆漿。不吃剩下的食物,他就會諄諄說教一番節儉之道和世間人們無食之苦。孫先生自奉如此儉樸,但招待朋友卻極熱誠,惟恐招待不夠豐盛。朋友有困難,無不竭誠幫忙。對其兄嫂則極尊敬,大陸淪陷之後,孫先生的長兄一家得能逃來臺灣,孫先生盡了很大的力量。娛樂方面,偶爾聽聽平劇,有時亦聽中國歌曲。在後園種菜是唯一的消遣兼運動,因為孫先生情感豐富,所以亦喜歡做做詩。做事方面,孫先生極認真,我記得有一次二位同學約了孫先生第二天早上八點鐘談話,但這位同學於八點一刻才到孫先生辦公室,孫先生即告以守時的重要,並把那次約會取消而重訂約會,其他方面就可以舉一反三了。
無論是工作、研究,甚至飲酒,我都不能與孫先生比,唯一我們二人程度差不多的是對國家的熱愛,這也是我們能超越了空間相交的理由。
以上就我所認識孫觀漢先生的工作、成就、他的個性為人等,作了一個流水帳式的報導,假如能有助於讀者孫先生的瞭解,進而對他所寫的文章有更深切的體會的話,那就是萬幸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於臺灣新竹清華大學
摘自星光版「關懷與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