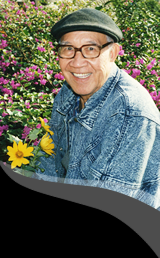
白髮和情書
潘秀玲
兩個月前,孫觀漢先生,許多年輕朋友們的「孫伯伯」,寄來他的新書「我看中國女人」,書上附言:「希望你寫兩篇書評,一篇在目前寫;一篇等妳到了我的年齡再寫。」另外加上一個條件:「請勿用壽慶式或訃文式!」收到書時我很興奮,立刻回信答說沒有問題。當時自以為對孫伯伯的人與書已十分熟悉,心中又是友情滿載,於情於理都有許多可寫,沒料到此一承諾竟成了我暑假以來最大的精神負擔,日夜塗寫總不成篇,一天比一天著急,仍得按捺性子再改寫下去。遙想三、四十年後,尚有另一篇待寫,不免也暗自擔心。
這樣猶豫難言,原因無他,第一,寫作本是痛苦的經驗;其次便是出於對孫伯伯的熟悉與友情,說來矛盾但的確如此。此刻當我面窗而坐,尋思在清華工作的日子。從一九八一年三月認識孫伯伯以後的一年裡,幾乎天天與他見面,偶爾兩三天不見便不禁想念,這是孫伯伯的親和力使然!很自然的,對他的信賴親近已使我很難客觀,再加上對他的日常思想感受,以至於習慣偏好都已那麼熟悉,而他書中所透露的訊息,一一可藉觀察他的生活得來,也使我難免先把書上所寫看成理所當然,而不去深思作者的苦心與見解獨到處。
但是,反過來說,對孫伯伯的熟悉也使我對他的書有更深一層的同情與了解。
孫伯伯自大學畢業後出國,直到退休,在外一共四十年。一九五九年他首度回國,內心的波動使他開始觀察和沈思中國社會的問題。「菜園懷臺雜思」「菜園裡的心痕」「菜園拾愛」和「關懷與愛心」等書,代表他從那時起的心路歷程,他將這些書比喻為對祖國懷念的一束「情書」。
十多年前,在給忘年的知己─十六歲的寒霧的信上,孫伯伯提醒她;年輕的愛國有若談戀愛,談時情濃,持久卻少;愈是情濃,一旦受到限制或打擊,當事人愈容易心灰意冷。因此他建議,對國家的關愛,最好像西方的這個詩句:
請稍稍的愛我,
請長久的愛我。
不僅給人建議,孫伯伯也證明他自己的「愛情」並非「天上的雲」,而是菜園裡的一顆種籽不斷在發榮滋長。十多年來,他在國外完成了上述的幾本書,回來定居後,在兩年內更寫了「有心的地方」和出版不久的「我看中國女人」兩本書。朋友們或會驚訝於他的愛心和毅力;而他當年開始紀錄這類思感的時候,恐怕也沒預料到二十年後,竟然在科學本行之外,結出別具滋味的另一個碩果。
孫伯伯剛回來時,有過一段消沈的日子。
偶爾看到他笑容底下的抑鬱,猜想他尚未適應國內的生活,但仍不能體會他的心境。陰雨綿綿的三月天,他待在屋裡喝酒,一杯一杯緩緩地喝,不停地喝。朋友來看他,一進門迎面便撲來滿室濃濃的酒氣,不禁都為他擔心。
孫伯伯借酒澆愁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的大兒子,自幼被認為天才,卻在六○年代嬉皮的浪潮中,因服食LSD而腦神經受傷,引發自殺殺人的傾向。孫伯伯對他又愛又怕又傷痛,用盡心力但似乎都無效;其二源自孫伯伯對中國的心痛與熱望。多年來他不斷自問問人:「為什麼中國人聰明、能幹、勤勞,但幾百年來建造不了一個康樂的國家?」孫伯伯的文章一貫是口語化的親切樸實;敘事慢慢道來,說理冷靜、客觀,而語氣則十分委婉,似乎有無限耐心隨時準備坐下來,與你面對面長談、細談,但他事實上是個非常熱情而急切的人,尤其是當遇到此類問題的時候。他對素昧平生,才初次見面的人,談談便提出這個問題。
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剛開始總不假思索地回答:缺少合理的制度、百年來內憂外患、戰亂頻仍、人口過剩、教育僵化等,也有人說少了一個工業革命,落後太多,一時無法迎頭趕上,……孫伯伯則堅持這些果不是因,他相信人性是決定一個國家振作與否的大因素,而中國最可怕的敵人是每個人從社會遺傳的劣根性,也就柏楊所說的醬缸,例如:自私、不合作、口是心非、媚上欺下、髒亂、迷信……等,接下往往是一場辯論。
孫伯伯與朋友共處喜歡傾聽,開起玩笑卻又頑皮捉狹得像孩童一般;偶爾還會向你會心地眨眨眼,那是他最可愛的時刻;然而一談起上面的問題,他便沈不住氣了,話說得既長又急,毫不放鬆,完全是苦口婆心式的囉嗦,又因他那口「紹興國語」,聽得人招架不住,覺得簡直跟他有理說不清。
初識孫伯伯的頭一個月裡,常被捲入此類混戰,待頭昏腦脹地回到宿舍,不免嘆一聲何苦,畢竟這種問種既無標準答案,個人也是無能為力的啊!
要真正了解一個人並不容易,很慢很慢我才懂得孫伯伯的用心,然後才懂得慚愧。當我們慷慨激昂討論「大問題」「大道理」時,孫伯伯卻汲汲於廁所、口水與抹布、當街便尿等「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事」。許多我們從小習慣的現象都足以讓他看了難過,偏偏還要睜大眼睛看,然後關起門來沈思,一個字一個字用心熬成文章或講稿。
孫伯伯的消沈正因為他用情太深,看事又看得太清楚。乍回國內,他看不慣的每一個現象令他震驚、痛心。例如:隨地吐痰在中國形同國粹,我們已能視若不見;然而有一回孫伯伯在國軍文藝中心觀賞國劇,竟因受不了鄰座觀眾大模大樣的吐痰而半途逃出場,從臺北趕回新竹,一夜煩心睡不著覺。他對吐痰的人無意深究,他憂心的毋寧是周遭人們無所謂的態度,是我們這個縱容人們隨地吐痰的社會。習之中人的我們見怪不怪,覺得這是「閒事」,他卻強調「見怪打怪」,並且他總有行動,這證諸於他的言行、書信、甚至於實驗報告。
孫伯伯在美國討論中國事的心情,他曾自喻是一個出嫁女兒對娘家的眷念,相夫教子之餘不忘寫信叮嚀娘家多保重身心;下雨的時日不免心念娘家漏雨的老屋;念著父母的老毛病,便千方百計尋遍藥方寄回來。……
等到孫伯伯回國時日一久,他的心情無法不跟著環境轉變。這好比出嫁的女兒對娘家的窘困,自個兒兄弟姊妹的脾氣長短,原先都已了然於心,在外掛念之餘不免殷殷問訊或叮嚀;如今回家長住,家裡頭大大小小的事一一看在眼裡,以前掛心的問題還是懸在那兒沒有解決,她回家的興奮很快就被更深的焦慮所取代,但是光心焦沒有用,她得做些什麼才行。於是她站起來先走進廚房幫忙,看到地髒了就掃,鍋子油污了就刷。
一陣子消沈以後,孫伯伯開始振作起來。
他相信:中國有病。有識之士如魯迅、柏楊等已將病態寫得十分透徹,並指出中國社會如一大醬缸,我們每個人生來便泡在其中而不自覺。這個觀念給了孫伯伯很大的啟發。但當孫伯伯請柏楊直接了當簡單說明什麼是「醬缸」時,這位原發明家多年來一直沒有提供明確的答覆。孫伯伯所受的科學訓練使他不甘如此罷休,於是自己開始埋頭苦思。
結果便是「老昏病」的發明。在「我看中國女人」一書中,孫伯伯對老昏病的病名、病型、病態、病害、病源、病根,乃至醫療的方法都有明確的解釋。
年近七十的孫伯伯最讓年輕朋友們感到壓力的是他的行動精神。許多時候路見不平不滿,我們只是發發牢騷就算了,孫伯伯總勸我們記下來,以免日後忘了,自己也犯同樣的錯誤。孫伯伯在西屋公司擔任的是放射線與核子研究兩個部門的主管,可能由於他長久的自我訓練,平日與他相處,常覺得他是個愛做事和少見的能做事的人。他不僅思慮精密,能想到別人想不到的細部問題,實行起來虛心謹慎,又有高度效率,結果往往是功德圓滿。相形之下,我們這些年輕人就顯得頭腦不清,做事拖拖拉拉,似乎是行將就木的老人。
孫伯伯回來的幾個月內,臺灣正大肆流行肝炎,報上宣稱百分之二十的人患肝炎,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帶肝炎菌。這樣聳人聽聞的數目似乎只是危者自危的說法,一般人總相信輪不到自己。君不見小吃攤上、大餐館裡大家共餐時筷子交錯,其樂融融的景象依舊在,似乎沒想到交換口水可能染上肝炎的危機。為了證明這種傳統吃法的不衛生,孫伯伯利用清大原子科學院的設備做了一個實驗,結果發現:假若有十個人共餐,用各自的筷子和湯匙在公盤公碗中取菜取湯,每人口中約有百分之三十的口水傳到公盤公碗,平均分配,每人所吃到別人口水的總量,相當於一個人口中的口水的百分之三十左右──等於一對情侶熱吻後互相交換的口水量!
這篇實驗報告以「口水與抹布」為題刊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中華日報,曾引起一陣熱烈的反應,大眾傳播界也參與「公筷母匙」運動的宣傳和推行。不知鑼鼓沈寂後至今可改變了多少人的觀念和行動?我只知道,在我目前就讀的大學裡的醫學院附設醫院,凡是臺灣來的留學生前來就醫,醫生都會特別問一聲:「有沒有得過肝炎?」牙醫如此,婦產科對產婦的產前檢查尤其要驗明肝炎一項──對臺灣來的。
出國在外寂寞而想家,不過有個好處,就是可藉在不同的社會中的生活體驗,試著比較雙方的特色短長。比較時難免產生主觀的偏失,而且常有很深的困惑。
多少年來多少國人把我國落後的原因,與東西文化的比較擺在一起談,而許多問題也只是談談而已。而孫伯伯的感想是:表面上東是東,西是西似無法融合。但我們得從人的立場,找尋和追求做人的共同因素和共同目標,因為人是人,更理想的──人是仁。本著這個原則,孫伯伯以他在西方社會所深受的對事分析的科學態度和待人平等的觀念,把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標出,讓每個人在可見可行的範圍內用心用力。「國民最重要,落後的國民不會有前進的國家!」他常拿美、日國民的生活態度當作例子,目的就在提醒我們放下自傲自卑,從實際的生活中向別的民族學習。強調實地生活的學習這點是孫伯伯與許多討論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不同的地方,可能也是他最大的貢獻。
細心的讀者可能感覺到孫伯伯的文章充滿深思、巧喻,例如「迷你思感」中的短短一句:
「有如許多壞的傳統習慣,打不勝打。但我們還得有毅力,打死一個是一個。」
標題為「蚊蠅」。他的短文雜感如同他平日與朋友聊天時的機智幽默;他的長文如「愚蠢的人」、「我們要不要科學」等,則從「問題」、「假設」出發,層層推理,最能看出他的邏輯訓練和虛心求證的態度。其實,如果說幾乎他的每篇文章都是「詩與邏輯的結合」是一點不過分的。由於天性的質樸,又為了指出如何的道路,提供明確的指標,孫伯伯的書一向是簡單而親切的,看事從Common sense出發,敘事說理清晰實在,從不唱高調,不倚老賣老。舉出的事例則非常具體化、大眾化。落實在自己的土地上後,孫伯伯這種「近取譬」的態度更明顯了,對我們社會的批評也就更直接、更實際、更強烈。他彷彿在說:「我們不要再講太多話了,就談談吃飯、開車好了。」這一點是「有心的地方」與「我看中國女人」跟以前的幾本書稍微不同的地方。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點不同是出於作者的「別有用心」。孫伯伯最怕是麻木。當他在美國的水土上,對國內的接觸是透過朋友的往來或從新聞、雜誌、書籍中得來,對其中中國特具的醬氣,往往很敏感,馬上便嗅出來。現在日夜被中國的空氣緊緊包圍,他必須隨時保持警覺,才能避免「久而不聞其醬」。出於這種心理,他反而變得更敏感傷感,他的觸角便不斷探向身旁的環境。清華成功湖上的垃圾和大餐廳的蒼蠅固然令他受不了,「大學生看不到蒼蠅和垃圾」更不由得他不心驚了! 不懷好意的人或許會說這是潔癖在作祟,而了解他的朋友會很誠懇地告訴你,這是因為作者多年來的使命感使他這樣「看不開」。他的心願很單純,只是「希望這個聰明和實質上可愛的民族康復起來」!
其實,任何外加的解釋對孫伯伯都是多餘的。當我讀這本書時,幾回翻到「蘿蔔」這篇小小文學,都不禁微笑。這篇短文約三、四百字,是為「幼獅少年」寫的。文中敘作者的中學時代因社會貧困,學生在校中吃飯常吃不飽,便以大碗炒蘿蔔填肚。去國四十年,最感不過癮的是美國的蘿蔔「又小、又瘦、又乾、又硬,皮厚肉少,並且價錢也不便宜」,回國後,看到菜場成堆的「肥白大蘿蔔」,心中便有說不出的喜悅。他告訴少年們:
「近二、三百年來,祖國的民主精神、科學觀念和生活標準,都比不上西方的前進國家,其實一切的事,有如蘿蔔,只要國人真心的願意栽培,再加努力,應可培養和發展得很成功和可愛的!」
是這樣簡單而美好的心意,使他在悲哀中永遠保持著甜蜜的期待!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台北「中華日報」